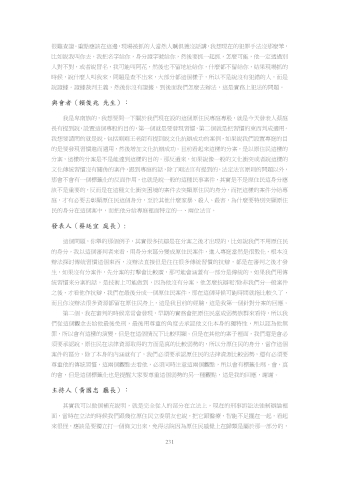Page 235 - 第四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235
很難查證。重點應該在這邊,現場被抓的人當然人贓俱獲沒話講,我想現在的犯罪手法沒那麼笨,
比如說我叫你去,我把名字給你,身分證字號給你,然後要抓一起抓,怎麼可能,他一定透過別
人對不對,或者說冒名,我可能叫阿花,然後也不留地址給你,什麼都不留給你,結果現場抓的
時候,說什麼人叫我來,問題是查不出來,大部分都這個樣子,所以不是說沒有犯錯的人,而是
說證據。證據裁判主義,然後你沒有證據,到後面我們怎麼去辦法,這是實務上犯法的問題。
與會者(賴俊兆 先生):
我是卑南族的,我想要問一下關於我們現在設的這個原住民專庭專股,就是今天發表人蔡庭
長有提到說,設置這個專股的目的,第一個就是要發現習慣,第二個就是把習慣的東西判成適用。
我想要請問的就是說,包括剛剛王老師有提到說文化抗辯成功的案例,如果說我們設置專庭的目
的是要發現習慣進而適用,然後增加文化抗辯成功。目前看起來這樣的分案,是以原住民這樣的
分案,這樣的分案是不是能達到這樣的目的。那反過來,如果說像一般的文化衝突或者說這樣的
文化傳統習慣沒有關係的案件,跟到專庭的話,除了剛法官有提到的,法定法官原則的問題以外,
那會不會有一個標籤化的反面作用,也就是說一般的這種民事案件,其實是不是原住民這身分應
該不是重要的,反而是在這種文化衝突困境的案件去突顯原住民的身分,而把這樣的案件分給專
庭,才有必要去彰顯原住民這個身分,至於其他什麼家暴、殺人、殺害,為什麼要特別突顯原住
民的身分在這個案中,而把他分給專庭裡面特定的一、兩位法官。
發表人(蔡廷宜 庭長):
這個問題,你舉的那個例子,其實很多抗辯是在分案之後才出現的,比如說我們不用原住民
的身分,我以這個審判者來看,用身分來區分變成原住民案件,進入專庭當然是很教化,根本沒
辦法探討傳統習慣這個東西,沒辦法直接但是往往很多傳統習慣的抗辯,都是在審判之後才發
生,如果沒有分案件,先分案的打擊會比較廣,那可能會涵蓋有一部分是傳統的,如果我們用傳
統習慣來分案的話,是技術上可能做到,因為他沒有分案,他怎麼抗辯呢?除非我們分一般案件
之後,才看他作抗辯,我們在最後分成一個原住民案件,那在這個時候可能時間就拖比較久了,
而且你沒辦法很多資源都留在原住民身上,這是我目前的經驗,這是我第一個針對分案的回應。
第二個,我在審判的時候常常會發現,早期的實務會把原住民當成弱勢族群來看待,所以我
們從這個觀念去給他最後免刑,最後用尊重的角度去承認他文化本身的獨特性,所以認為他無
罪,所以會有這樣的演變,但是在這個情況下比較明顯。但是在其他的案子裡面,我們還是會必
須要承認說,原住民在法律資源取得的方面是真的比較弱勢的,所以分原住民的身分,當作這個
案件的區分,除了本身的內涵就有了,我們必須要承認原住民的法律資源比較弱勢,還有必須要
尊重他的傳統習慣,這兩個觀點去看他,必須同時注意這兩個觀點,所以會有標籤化嗎。會,真
的會,但是這個標籤化也是提醒大家要尊重這個弱勢的另一種觀點,這是我的回應,謝謝。
主持人(黃國忠 廳長):
其實我可以做個補充說明,就是完全從人的部分在立法上,現在的刑事訴訟法強制辯論裡
面,當時在立法的時候我們跟幾位原住民立委朋友也說,把它跟醫療、智能不足擺在一起,看起
來很怪,應該是要獨立打一個條文出來,免得法院因為原住民感覺上在歸類是屬於那一部分的,
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