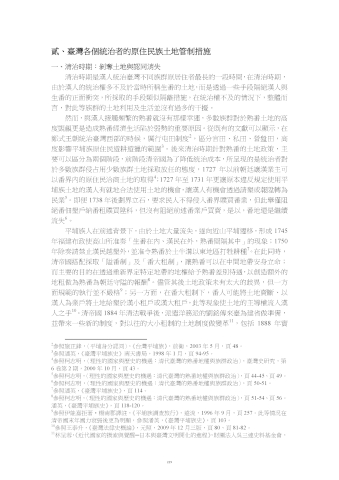Page 233 - 第六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233
貳、臺灣各個統治者的原住民族土地管制措施
一、清治時期:剝奪土地與認同消失
清治時期是漢人統治臺灣不同族群原居住者最長的一段時間,在清治時期,
由於漢人的統治權多不及於當時所稱生番的土地,而是透過一些手段隔絕漢人與
生番的正面衝突,所採取的手段類似隔離措施,在統治權不及的情況下,整體而
言,對此等族群的土地利用及生活並沒有過多的干擾。
然而,與漢人接觸頻繁的熟番就沒有那樣幸運,多數族群對於熟番土地的高
度覬覦更是造成熟番經濟生活陷於弱勢的重要原因。從既有的文獻可以顯示,在
2
鄭式王朝統治臺灣西部的時候,厲行屯田制度 ,區分官田、私田、營盤田,高
3
度影響平埔族原住民遊耕遊獵的範圍 。後來清治時期針對熟番的土地政策,主
要可以區分為兩個階段,前階段清帝國為了降低統治成本,所呈現的是統治者對
於多數族群侵占用少數族群土地採取放任的態度,1727 年以前朝廷讓漢業主可
4
以番界內的原住民洽商土地的取得;1727 年至 1731 年更讓原本違反規定使用平
埔族土地的漢人有就地合法使用土地的機會,讓漢人有機會透過請墾或報陞轉為
5
民業 。即便 1738 年後劃界立石,要求民人不得侵入番界贌買番業,但此舉僅阻
絕番佃墾戶納番租贌買陞科,但沒有阻絕前述番業戶買賣,是以,番地還是繼續
6
流失 。
平埔族人在前述背景下,由於土地大量流失,遂向近山平埔遷移,形成 1745
年福建布政使高山所准奏「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其中」的現象;1750
7
年除奏請禁止漢民越墾外,並准令熟番於土牛溝以東地區打牲耕種 。在此同時,
清帝國搭配採取「隘番制」及「番大租制」, 讓熟番可以在中間地帶安身立命;
而主要的目的在透過重新界定特定地帶的地權給予熟番差別待遇,以創造額外的
8
地租做為熟番為朝廷守隘的報酬 。儘管其後土地政策未有太大的歧異,但一方
9
面規範的執行並不嚴格 ;另一方面,在番大租制下,番人可能將土地賣斷、以
漢人為業戶將土地給墾於漢小租戶或漢大租戶,此等現象使土地的主導權流入漢
10
人之手 。清帝國 1884 年清法戰爭後,派遣洋務派的劉銘傳來臺為建省做準備,
11
並帶來一些新的制度,對以往的大小租制的土地制度做變革 ,包括 1888 年實
2 參照施正鋒,〈平埔身分認同〉,《台灣平埔族》,前衛,2003 年 5 月,頁 48。
3 參照潘英,《臺灣平埔族史》南天書局,1998 年 1 月,頁 94-95。
4 參照柯志明,〈理性的國家與歷史的機遇:清代臺灣的熟番地權與族群政治〉,臺灣史研究,第
6 卷第 2 期,2000 年 10 月,頁 43。
5 參照柯志明,〈理性的國家與歷史的機遇:清代臺灣的熟番地權與族群政治〉,頁 44-45、頁 49。
6 參照柯志明,〈理性的國家與歷史的機遇:清代臺灣的熟番地權與族群政治〉,頁 50-51。
7 參照潘英,《臺灣平埔族史》,頁 114。
8 參照柯志明,〈理性的國家與歷史的機遇:清代臺灣的熟番地權與族群政治〉,頁 51-54、頁 56。
潘英,《臺灣平埔族史》,頁 118-120。
9 參照伊能嘉拒著‧楊南郡譯註,《平埔族調查旅行》,遠流,1996 年 9 月,頁 257。此等情況在
清帝國末年國力衰弱後更為明顯,參照潘英,《臺灣平埔族史》,頁 103。
10 參照王泰升,《臺灣法律史概論》,元照,2009 年 12 月三版,頁 80、頁 81-82。
11 林呈蓉,《近代國家的摸索與覺醒─日本與臺灣文明開化的進程》,財團法人吳三連史料基金會,
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