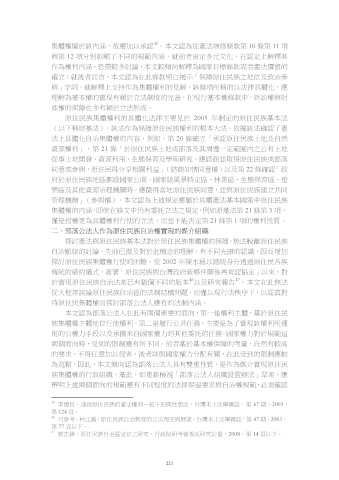Page 227 - 第七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227
45
集體權屬於該內涵,故應加以承認 。本文認為從憲法增修條款第 10 條第 11 項
與第 12 項分別彰顯了不同的規範內涵,就前者肯定多元文化,在認定上解釋其
作為權利內涵,恐需較多討論,本文較傾向解釋為國家目標條款或者憲法價值的
確立;就後者而言,本文認為在此條款明白揭示「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
與」字詞,就解釋上支持作為集體權利的見解,該條項所稱的以法律具體化,應
理解為基本權的實現有賴於立法制度的完善,在現行基本權條款中,訴訟權與財
產權的保障也多有賴於立法形成。
原住民族集體權利的具體化法律主要見於 2005 年制定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以下稱原基法),該法作為保障原住民族權利的根本大法。依據該法確認了憲
法上具體化自治集體權的內容,例如,第 20 條確立「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
資源權利」、第 21 條「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
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諮商知情同意權)以及第 22 條確認「政
府於原住民族地區劃設國家公園、國家級風景特定區、林業區、生態保育區、遊
樂區及其他資源治理機關時,應徵得當地原住民族同意,並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
管理機制」(參與權)。本文認為上述規定應屬於具體憲法基本國策中原住民族
集體權的內涵,即使在條文中仍有委託立法之規定,例如原基法第 21 條第 3 項,
僅是授權更為具體權利行使的立法,而並不能否定第 21 條第 1 項的權利性質。
二、部落公法人作為原住民族自治權實現的媒介組織
探討憲法與原住民族基本法對於原住民族集體權的保障,無法脫離原住民族
自治脈絡的討論。先前已提及對於此概念的理解,有不同光譜的認識,因而增加
探討原住民族集體權行使的困難。從 2002 年陳水扁以總統身分透過原住民各族
傳統的締約儀式,簽署「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夥伴關係再肯認協定」以來,對
47
46
於實現原住民族自治法案已有數個不同的版本 以及研究報告 。本文在此無法
從大框架談論原住民族自治區的法制結構問題,而僅以現行法秩序下,以認真對
待原住民集體權而探討部落公法人應有的法制內涵。
本文認為部落公法人在此有兩個重要的面向,第一是權利主體,基於原住民
族集體權主體地位行使權利,第二是履行公共任務,主要是為了實現該權利所運
用的公權力手段以及承擔來自國家權力的其他委託的任務。國家權力對於規範這
兩個面向時,受到的限制應有所不同。前者基於基本權保障的考量,自然有較高
的要求,不得任意加以侵害,後者則與國家權力分配有關,在此受到的限制應較
為寬鬆。因此,本文傾向認為部落公法人具有雙重性質,是作為媒介實現原住民
族集體權的行政組織。基此,如重新檢視「部落公法人組織設置辦法」草案,應
辨明上述兩個面向的規範應有不同程度的法律保留要求與自治權規範,必須確認
45 李建良,淺說原住民族的憲法權利—若干初探性想法,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7 期,2003,
第 124 頁。
46 可參考,林江義,原住民族自治制度的立法現況與展望,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7 期 , 2003,
第 77 頁以下。
47 施正鋒,原住民族自治區定位之研究,行政院研考會委託研究計畫,2008,第 14 頁以下。
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