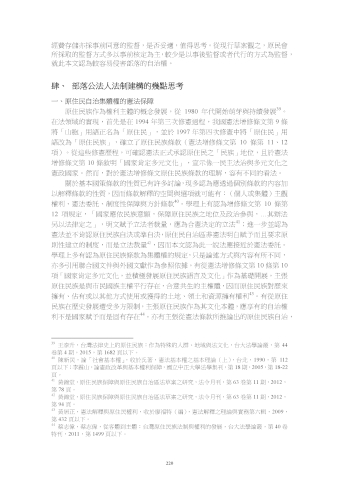Page 226 - 第七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226
經費存儲亦採事前同意的監督,是否妥適,值得思考。從現行草案觀之,原民會
所採取的監督方式多以事前核定為主,較少是以事後監督或者代行的方式為監督,
就此本文認為較容易侵害部落的自治權。
肆、 部落公法人法制建構的幾點思考
一、原住民自治集體權的憲法保障
39
原住民族作為權利主體的概念發展,從 1980 年代開始萌芽與持續發展 。
在法領域的實現,首先是在 1994 年第三次修憲過程,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
將「山胞」用語正名為「原住民」,並於 1997 年第四次修憲中將「原住民」用
語改為「原住民族」,確立了原住民族條款(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12
項)。從這些修憲歷程,可確認憲法正式承認原住民之「民族」地位,且於憲法
增修條文第 10 條敘明「國家肯定多元文化」,宣示係一民主法治與多元文化之
憲政國家。然而,對於憲法增修條文原住民族條款的理解,容有不同的看法。
關於基本國策條款的性質已有許多討論,現多認為應透過個別條款的內容加
以解釋條款的性質,因而條款解釋的空間與選項就可能有:(個人或集體)主觀
40
權利、憲法委託、制度性保障與方針條款 。學理上有認為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2 項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其辦法
41
另以法律定之」,明文賦予立法者裁量,應為合憲決定的立法 ;進一步並認為
憲法並不肯認原住民族自決或準自決,原住民自治區非憲法明白賦予而且要求原
42
則性建立的制度,而是立法裁量 ,因而本文認為此一說法應接近於憲法委託。
學理上多有認為原住民族條款為集體權的規定,只是論述方式與內容有所不同,
亦多引用聯合國文件與外國文獻作為參照依據。有從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0
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作為基礎開展,主張
原住民族是與市民國族主權平行存在,合意共生的主權體,因而原住民族對歷來
43
擁有、佔有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或獲得的土地、領土和資源擁有權利 。有從原住
民族在歷史發展遭受多方限制,主張原住民族作為其文化本體,應享有的自治權
44
利不是國家賦予而是固有存在 。亦有主張從憲法條款所推論出的原住民族自治,
39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上的原住民族:作為特殊的人群、地域與法文化,台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第 4 期,2015,第 1682 頁以下。
40 陳新民,論「社會基本權」,收於氏著,憲法基本權之基本理論(上),台北,1990,第 112
頁以下;李震山,論憲政改革與基本權利保障,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18 期 , 2005, 第 18-22
頁。
41 黃錦堂,原住民族保障與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之研究,法令月刊,第 63 卷第 11 期,2012,
第 78 頁。
42 黃錦堂,原住民族保障與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之研究,法令月刊,第 63 卷第 11 期,2012,
第 94 頁。
43 黃居正,憲法解釋與原住民權利,收於廖福特(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六輯,2009,
第 432 頁以下。
44 蔡志偉,蔡志偉,從客體到主體:台灣原住民族法制與權利的發展,台大法學論叢,第 40 卷
特刊,2011,第 1499 頁以下。
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