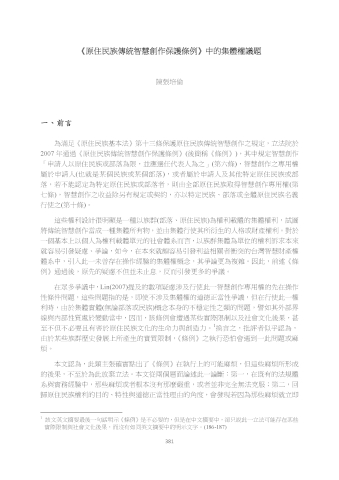Page 385 - 第一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385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中的集體權議題
陳張培倫
一、前言
為滿足《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三條保護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之規定,立法院於
2007 年通過《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後簡稱《條例》),其中規定智慧創作
「申請人以原住民族或部落為限,並應選任代表人為之」(第六條),智慧創作之專用權
屬於申請人(也就是某個民族或某個部落),或者屬於申請人及其他特定原住民族或部
落,若不能認定為特定原住民族或部落者,則由全部原住民族取得智慧創作專用權(第
七條),智慧創作之收益除另有規定或契約,亦以特定民族、部落或全體原住民族名義
行使之(第十條)。
這些權利設計很明顯是一種以族群(部落、原住民族)為權利載體的集體權利,試圖
將傳統智慧創作當成一種集體所有物,並由集體行使其所衍生的人格或財產權利。對於
一個基本上以個人為權利載體單元的社會體系而言,以族群集體為單位的權利訴求本來
就容易引發疑慮、爭論,如今,在本來就頗容易引發利益相關者衝突的台灣智慧財產權
體系中,引入此一未曾存在操作經驗的集體權概念,其爭論更為複雜。因此,前述《條
例》通過後,原先的疑慮不但並未止息,反而引發更多的爭議。
在眾多爭議中,Lin(2007)提及的數項疑慮涉及行使此一智慧創作專用權的先在操作
性條件問題,這些問題指的是,即使不涉及集體權的道德正當性爭議,但在行使此一權
利時,由於集體實體(無論部落或民族)概念本身的不穩定性之類的問題,譬如其外部界
線與內部性質處於變動當中,因而,該條例會遭遇某些實際限制以及社會文化後果,甚
1
至不但不必要且有害於原住民族文化的生命力與創造力。 換言之,批評者似乎認為,
由於某些族群歷史發展上所產生的實質限制,《條例》之執行恐怕會遇到一此問題或麻
煩。
本文認為,此類主張確實點出了《條例》在執行上的可能麻煩,但這些麻煩所形成
的後果,不至於為此放棄立法。本文從兩個層面論述此一論斷:第一,在既有的法規體
系與實務經驗中,那些麻煩或者根本沒有那麼嚴重,或者並非完全無法克服;第二,回
歸原住民族權利的目的、特性與道德正當性理由的角度,會發現若因為那些麻煩就立即
1 該文英文摘要最後一句話明示《條例》是不必要的,但是在中文摘要中,卻只說此一立法可能存在某些
實際限制與社會文化後果,而沒有如同英文摘要中的明示文字。(186-187)
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