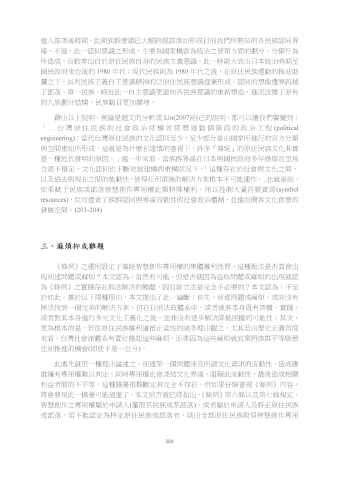Page 388 - 第一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388
進入部落後時期,此期族群意識已大幅跨越部落而形成目前我們所熟知的各民族認同界
線,不過,此一認同意識之形成,主要為國家機器為統治之便單方面的劃分、分類行為
所造成,而較非出自於原住民族自身的民族主義意識,此一時期大致由日本統治時期至
國民政府來台後的 1980 年代;現代民族則為 1980 年代之後,在原住民族運動的推波助
瀾之下,具有民族主義自主意識精神的泛原住民族意識逐漸形成,認同的想像邊界跨越
了部落、單一民族。晚近此一自主意識更迴向各民族意識的重新塑造,進而改變了原有
的九族劃分結構,民族數目更加擴增。
藉由以上說明,無論是趙文的分析或 Lin(2007)自己的說明,都可以讓我們警覺到:
「 … 台 灣 原 住 民 族 的 社 會 政 治 結 構 曾 經 歷 過 數 個 階 段 的 政 治 工 程 (political
engineering);當代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認同至少,至少部分是由國家所進行的官方分類
與空間重組所形成。這就是為什麼在謹慎的審視下,許多『傳統』的原住民族文化其實
是一種近代發明的原因。」進一步來看,當族群界線在日本與國民政府多年操縱而呈現
含混不穩定,文化認同也不斷地被建構與重構狀況下,「這種存在於社會與文化之間,
以及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能動性,使得任何單純的解決方案根本不可能運作。」也就是說,
如果賦予民族或部落智慧創作專用權此類特殊權利,用以控制大量符號資源(symbol
resources),反而違背了族群認同與界線流動性的社會政治體制,並進而傷害文化創意的
發展空間。(203-204)
三、麻煩抑或難題
《條例》之運用設定了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的集體權利性質,這種做法是否真會出
現前述問題或麻煩?本文認為:當然有可能。但是否就因為這些問題或麻煩的出現就認
為《條例》之實踐存在無法解決的難題,因而該立法是完全不必要的?本文認為:不至
於如此。基於以下兩種理由,本文提出了此一論斷:首先,前述問題或麻煩,或許沒有
辦法找到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但在目前法政體系中,或者就其本身既有架構、實踐,
或者對其本身進行多元文化主義化之後,並非沒有逐步解決降低困擾的可能性;其次,
更為根本的是,若從原住民族權利道德正當性的諸多理由觀之,尤其若由歷史正義角度
來看,台灣社會諸體系有責任擔起這些麻煩,而非因為這些麻煩就放棄將族群平等願景
往前推進的機會(即使不是一百分)。
此處先就第一種理由論述之。前述第一個問題涉及所謂文化資訊的流動性,造成應
誰擁有專用權難以判定,同時專用權也會凍結文化界線,阻礙此流動性,最後造成相關
利益者間的不平等。這種擔憂很難斷定其完全不存在,但如果仔細審視《條例》內容,
將會發現此一擔憂可能過慮了。本文前言就已經指出,《條例》第六條以及第七條規定,
智慧創作之專用權屬於申請人(僅限某民族或某部落),或者屬於申請人及特定原住民族
或部落,若不能認定為特定原住民族或部落者,則由全部原住民族取得智慧創作專用
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