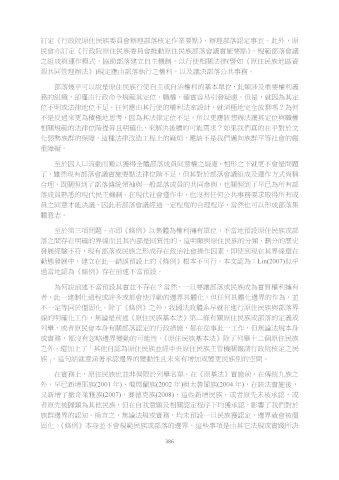Page 390 - 第一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390
訂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部落核定作業要點》,辦理部落認定事宜。此外,原
民會亦訂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部落會議實施要點》,規範部落會議
之組成與運作模式,協助部落建立自主機制,以行使相關法律(譬如《原住民族地區資
源共同管理辦法》)規定應由部落執行之權利,以及議決部落公共事務。
部落幾乎可以說是原住民族行使自主或自治權利的基本單位,此類涉及重要權利義
務的組織,卻僅由行政命令規範其定位、職權,確實容易引發疑慮。但是,就因為其定
位不明或法律地位不足,任何應由其行使的權利法案設計,就消極地完全放棄嗎?為何
不是反過來更為積極地思考,因為其法律定位不足,所以更應該想辦法讓其定位與職權
相關規範的法律位階提昇且明確化,來解決後續的可能需求?如果我們真的在乎對於文
化弱勢族群的保障,這種法律改造工程上的麻煩,應該不是我們邁向族群平等社會的嚴
重障礙。
至於因人口流動而難以獲得全體部落成員同意權之疑慮,相形之下就更不會是問題
了,雖然現有部落會議實施要點法律位階不足,但其對於部落會議組成及運作方式尚稱
合理,既關照到了部落傳統領袖與一般部落成員的共同參與,也關照到了早已為所有部
落成員熟悉的現代民主機制。在現代社會運作中,也沒有任何公共事務要求取得所有成
員之同意才能決議,因此若部落會議經過一定程度的合理程序,當然也可以形成部落集
體意志。
至於第三項問題,亦即《條例》以集體為權利擁有單位,不當地預設原住民族或部
落之間存在明確的界線而且其內部是同質性的,這明顯與原住民族的分類、劃分的歷史
發展經驗不符,現有部落或民族之形成存在政治社會操作因素,即使到現在其界線還在
動態發展中,建立在此一錯誤預設上的《條例》根本不可行。本文認為:Lin(2007)似乎
過當地認為《條例》存在前述不當預設。
為何說前述不當預設其實並不存在?當然,一旦要讓部落或民族成為實質權利擁有
者,此一建制化過程或許多或都會使浮動的邊界具體化,但任何具體化邊界的作為,並
不一定等同於僵固化。除了《條例》之外,我國法政體系早就在進行原住民族與部落界
線的明確化工作,無論是前述《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有關原住民族或部落的定義或
列舉,或者原民會本身有關部落認定的行政措施,都在從事此一工作,但無論法規本身
或實務,都沒有忽略邊界變動的可能性。《原住民族基本法》除了列舉十二個原住民族
之外,還加上了 「 其他自認為原住民族並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民
族」,這句話就意涵著承認邊界的變動性且未來有增加或變更民族別的空間。
在實務上,原住民族也並非侷限於列舉名單,在《原基法》實施前,在傳統九族之
外,早已新增邵族(2001 年)、噶瑪蘭族(2002 年)與太魯閣族(2004 年),在該法實施後,
又新增了撤奇萊雅族(2007)、賽德克族(2008),這些新增民族,或者原先未被承認,或
者原先被歸類為其他民族,但在自我意願及相關認定程序下均獲承認,影響了我們對於
族群邊界的認知。換言之,無論法規或實務,均未預設一旦民族獲認定,邊界就會被僵
固化。《條例》本身並不會規範民族或部落的邊界,這些事項是由其它法規或實踐所決
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