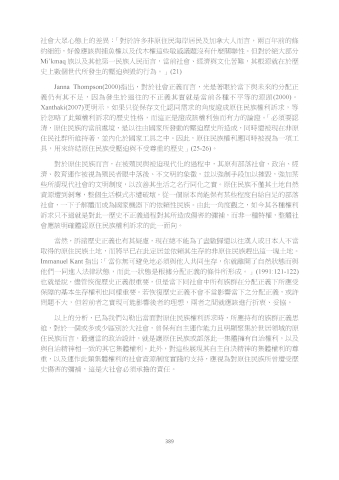Page 393 - 第一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393
社會大眾心態上的差異:「對於許多非原住民海岸居民及加拿大人而言,兩百年前的條
約細節,好像應該與捕魚權以及伐木權這些敏感議題沒有什麼關聯性。但對於絕大部分
Mi’kmaq 族以及其他第一民族人民而言,當前社會、經濟與文化苦難,其根源就在於歷
史上數個世代所發生的壓迫與毀約行為。」(21)
Janna Thompson(2000)指出,對於社會正義而言,光是著眼於當下與未來的分配正
義仍有其不足,因為發生於過往的不正義其實就是當前各種不平等的源頭(2000)。
Xanthaki(2007)更明示,如果只從保存文化認同需求的角度證成原住民族權利訴求,等
於忽略了此類權利訴求的歷史性格,而這正是證成該權利強而有力的論證。「必須要認
清,原住民族的當前處境,是以往由國家所發動的壓迫歷史所造成,同時還被現在非原
住民社群所維持著,並內化於國家工具之中。因此,原住民族權利應同時被視為一項工
具,用來終結原住民族受壓迫與不受尊重的歷史」(25-26)。
對於原住民族而言,在被殖民與被迫現代化的過程中,其原有部落社會、政治、經
濟、教育運作被視為殖民者眼中落後、不文明的象徵,並以強制手段加以摧毀,強加某
些所謂現代社會的文明制度,以改善其生活之名行同化之實。原住民族不僅其土地自然
資源遭到剝奪,整個生活模式亦遭破壞,從一個原本尚能保有某些程度自給自足的部落
社會,一下子解體而成為國家機器下的依賴性民族。由此一角度觀之,如今其各種權利
訴求只不過就是對此一歷史不正義過程對其所造成傷害的彌補,而非一種特權,整體社
會應該明確體認原住民族權利訴求的此一面向。
當然,訴諸歷史正義也有其疑慮,現在總不能為了盡數歸還以往漢人或日本人不當
取得的原住民族土地,而將早已在此定居並依賴其生存的非原住民族趕出這一塊土地。
Immanuel Kant 指出:「當你無可避免地必須與他人共同生存,你就離開了自然狀態而與
他們一同進入法律狀態,而此一狀態是根據分配正義的條件所形成。」(1991:121-122)
也就是說,儘管恢復歷史正義很重要,但是當下同社會中所有族群在分配正義下所應受
保障的基本生存權利也同樣重要。若恢復歷史正義不會不當影響當下之分配正義,或許
問題不大,但若前者之實現可能影響後者的理想,兩者之間就應該進行折衷、妥協。
以上的分析,已為我們勾勒出當面對原住民族權利訴求時,所應持有的族群正義思
維,對於一個或多或少區別於大社會,曾保有自主運作能力且明顯聚集於世居領域的原
住民族而言,最適當的政治設計,就是讓原住民族或部落此一集體擁有自治權利,以及
與自治精神相一致的其它集體權利。此外,對這些展現其自主自決精神的集體權利的尊
重,以及運作此類集體權利的社會資源制度實踐的支持,應視為對原住民族所曾遭受歷
史傷害的彌補,這是大社會必須承擔的責任。
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