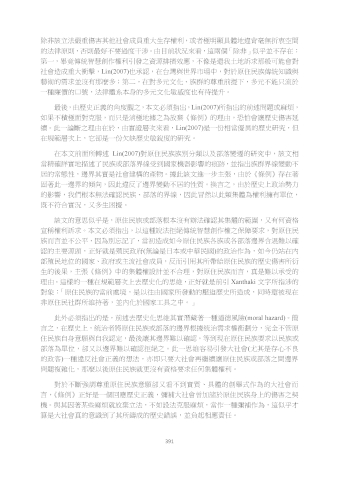Page 395 - 第一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395
除非該立法嚴重傷害其他社會成員重大生存權利,或者極明顯具體地違背毫無折衷空間
的法律原則,否則最好不要過度干涉。由目前狀況來看,這兩個「除非」似乎並不存在:
第一,畢竟傳統智慧創作權利引發之資源排擠效應,不像是還我土地訴求那般可能會對
社會造成重大衝擊,Lin(2007)也承認,在台灣與世界市場中,對於原住民族傳統知識與
藝術的需求並沒有那麼多;第二,在對多元文化、族群的尊重前提下,多元不能只流於
一種廉價的口號,法律體系本身的多元文化敏感度也有待提升。
最後,由歷史正義的角度觀之,本文必須指出,Lin(2007)所指出的前述問題或麻煩,
如果不積極面對克服,而只是消極地據之為放棄《條例》的理由,恐怕會讓歷史傷害延
續。此一論斷之理由在於,由實證層次來看,Lin(2007)是一份相當優異的歷史研究,但
在規範層次上,它卻是一份欠缺歷史敏銳度的研究。
在本文前面所轉述 Lin(2007)對原住民族族別分類以及部落變遷的研究中,該文相
當精確詳實地描述了民族或部落界線受到國家機器影響的痕跡,並指出族群界線變動不
居的常態性,邊界其實是社會建構的產物。據此該文進一步主張,由於《條例》存在著
固著此一邊界的傾向,因此違反了邊界變動不居的性質。換言之,由於歷史上政治勢力
的影響,我們根本無法確認民族、部落的界線,因此冒然以此類集體為權利擁有單位,
既不符合實況,又多生困擾。
該文的意思似乎是,原住民族或部落根本沒有辦法確認其集體的範圍,又有何資格
宣稱權利訴求。本文必須指出,以這種說法拒絕傳統智慧創作權之保障要求,對原住民
族而言並不公平,因為別忘記了,當初造成如今原住民族各族或各部落邊界含混難以確
認的主要源頭,正好就是殖民政府(無論是日本或中華民國)的政治作為,如今仍站在內
部殖民地位的國家、政府或主流社會成員,反而引用其所帶給原住民族的歷史傷害所衍
生的後果,主張《條例》中的集體權設計並不合理,對原住民族而言,真是難以承受的
理由。這樣的一種在規範層次上去歷史化的思維,正好就是前引 Xanthaki 文字所指涉的
對象:「原住民族的當前處境,是以往由國家所發動的壓迫歷史所造成,同時還被現在
非原住民社群所維持著,並內化於國家工具之中。」
此外必須指出的是,前述去歷史化思維其實潛藏著一種道德風險(moral hazard)。簡
言之,在歷史上,統治者將原住民族或部落的邊界根據統治需求權衡劃分,完全不管原
住民族自身意願與自我認定,最後讓其邊界難以確認。等到現在原住民族要求以民族或
部落為單位,卻又以邊界難以確認拒絕之。此一思維容易引發大社會(尤其是存心不良
的政客)一種違反社會正義的想法,亦即只要大社會再繼續讓原住民族或部落之間邊界
問題複雜化,那麼以後原住民族就更沒有資格要求任何集體權利。
對於不斷強調尊重原住民族意願卻又看不到實質、具體的創舉式作為的大社會而
言,《條例》正好是一個回應歷史正義,彌補大社會曾加諸於原住民族身上的傷害之契
機。與其因著某些麻煩就放棄立法,不如設法克服麻煩,當作一種彌補作為,這似乎才
算是大社會真的意識到了其所鑄成的歷史錯誤,並負起相應責任。
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