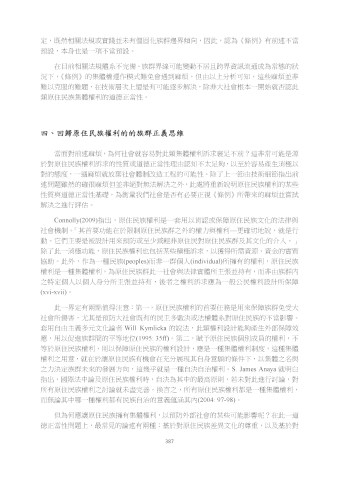Page 391 - 第一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391
定,既然相關法規或實踐並未有僵固化族群邊界傾向,因此,認為《條例》有前述不當
預設,本身也是一項不當預設。
在目前相關法規體系不完備、族群界線可能變動不居且跨界資訊流通成為常態的狀
況下,《條例》的集體權運作模式難免會遇到麻煩,但由以上分析可知,這些麻煩並非
難以克服的難題,在技術層次上還是有可能逐步解決,除非大社會根本一開始就否認此
類原住民族集體權利的道德正當性。
四、回歸原住民族權利的的族群正義思維
當面對前述麻煩,為何社會就容易對此類集體權利訴求裹足不前?這非常可能是源
於對原住民族權利訴求的性質或道德正當性理由認知不太足夠,以至於容易產生消極以
對的態度,一遇麻煩就放棄社會體制改造工程的可能性。除了上一節由技術細節指出前
述問題雖然的確很麻煩但並非絕對無法解決之外,此處將重新說明原住民族權利的某些
性質與道德正當性基礎,為衡量我們社會是否有必要正視《條例》所帶來的麻煩並嘗試
解決之進行評估。
Connolly(2009)指出,原住民族權利是一套用以肯認或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的法律與
社會機制。「其首要功能在於限制原住民族群之外的權力與權利—更確切地說,就是行
動。它們主要是被設計用來預防或至少減輕非原住民對原住民族群及其文化的介入。」
除了此一消極功能,原住民族權利也包括某些積極訴求,以獲得所需資源、資金的實質
協助。此外,作為一種民族(peoples)而非一群個人(individual)所擁有的權利,原住民族
權利是一種集體權利,為原住民族群此一社會與法律實體所主張並持有,而非由族群內
之特定個人以個人身分所主張並持有,後者之權利訴求應為一般公民權利設計所保障
(xvi-xvii)。
此一界定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原住民族權利的首要任務是用來保障族群免受大
社會所傷害,尤其是預防大社會既有的民主多數決或法權體系對原住民族的不當影響。
套用自由主義多元文化論者 Will Kymlicka 的說法,此類權利設計能夠產生外部保障效
應,用以促進族群間的平等地位(1995: 35ff)。第二,賦予原住民族個別成員的權利,不
等於原住民族權利,用以保障原住民族的權利設計,應是一種集體權利制度,這種集體
權利之用意,就在於讓原住民族有機會在充分展現其自身意願的條件下,以集體之名與
之力決定族群未來的發展方向,這幾乎就是一種自決自治權利。S. James Anaya 就明白
指出,國際法中論及原住民族權利時,自決為其中的最高原則,若未對此進行討論,對
所有原住民族權利之討論就未盡完善。換言之,所有原住民族權利都是一種集體權利,
而無論其中哪一種權利都有民族自治的意義蘊涵其內(2004: 97-98)。
但為何應讓原住民族擁有集體權利,以預防外部社會的某些可能影響呢?在此一道
德正當性問題上,最常見的論述有兩種:基於對原住民族差異文化的尊重,以及基於對
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