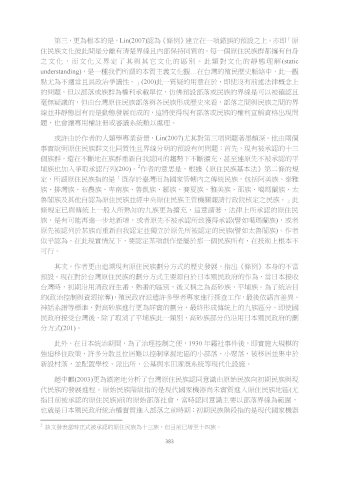Page 387 - 第一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387
第三,更為根本的是,Lin(2007)認為《條例》建立在一項錯誤的預設之上,亦即「原
住民族文化彼此間是分離有清楚界線且內部保持同質的。每一個原住民族群都擁有自身
之 文 化 , 而 文 化 又 界 定 了 其 與 其 它 文 化 的 區 別 。 此 類 對 文 化 的 靜 態 理 解 (static
understanding),是一種我們所謂的本質主義文化觀…在台灣的殖民歷史脈絡中,此一觀
點尤為不適當且具政治爭議性。」(200)此一質疑的用意在於,即使沒有前述法律概念上
的問題,但以部落或族群為權利承載單位,仿佛預設部落或民族的界線是可以被確認且
毫無疑議的,但由台灣原住民族部落與各民族形成歷史來看,部落之間與民族之間的界
線並非靜態固有而是動態發展而成的,這將使得現有部落或民族的權利宣稱資格出現問
題,也會讓專用權註冊或審議系統難以處理。
或許由於作者的人類學專業背景,Lin(2007)尤其對第三項問題著墨頗深。他由兩個
事實說明原住民族群文化同質性且界線分明的預設有何問題:首先,現有被承認的十三
個族群,還在不斷地在族群重新自我認同的趨勢下不斷擴充,甚至連原先不被承認的平
2
埔族也加入爭取承認行列(200)。 作者的意思是,根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的規
定,所謂原住民族指的是「既存於臺灣而為國家管轄內之傳統民族,包括阿美族、泰雅
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
魯閣族及其他自認為原住民族並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民族。」 此
條規定已與傳統上一般人所熟知的九族更為擴充,這意謂著,法律上所承認的原住民
族,是有可能再進一步地新增,或者原先不被承認所致獲得承認(譬如噶瑪蘭族),或者
原先被認列於某族而重新自我認定並獨立於原先所被認定的民族(譬如太魯閣族)。作者
似乎認為,在此現實情況下,要認定某項創作是屬於那一個民族所有,在技術上根本不
可行。
其次,作者更由追溯現有原住民族劃分方式的歷史發展,指出《條例》本身的不當
預設。現在對於台灣原住民族的劃分方式主要源自於日本殖民政府的作為,當日本接收
台灣時,初期沿用清政府生番、熟番的區別,後又稱之為高砂族、平埔族。為了統治目
的(政治控制與資源掠奪),殖民政府派遣許多學者專家進行探查工作,最後依語言差異、
神話系譜等標準,對高砂族進行更為詳實的劃分,最終形成傳統上的九族區分。即使國
民政府接受台灣後,除了取消了平埔族此一類別,高砂族部分仍沿用日本殖民政府的劃
分方式(201)。
此外,在日本統治期間,為了治理控制之便,1930 年霧社事件後,即實施大規模的
強迫移住政策,許多分散且位居難以控制掌握地區的小部落、小聚落,被移居並集中於
新設村落,並配置學校、派出所、公墓與水田灌溉系統等現代化設施。
趙中麒(2003)更為縝密地分析了台灣原住民族認同意識由原始民族向初期民族與現
代民族的發展進程。原始民族階級指的是現代國家機器尚未實質進入原住民族地區(尤
指目前被承認的原住民族)前的原始部落社會,當時認同意識主要以部落界線為範圍,
也就是日本殖民政府統治權實質進入部落之前時期;初期民族階段指的是現代國家機器
2 該文發表當時正式被承認的原住民族為十三族,但目前已增至十四族。
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