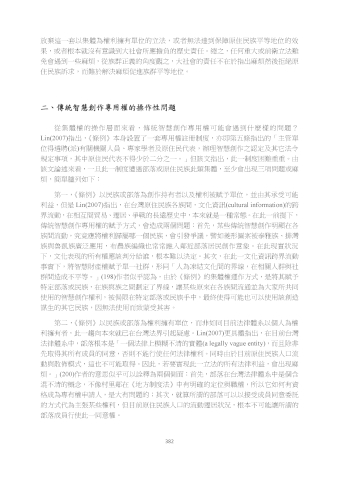Page 386 - 第一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386
放棄這一套以集體為權利擁有單位的立法,或者無法達到保障原住民族平等地位的效
果,或者根本就沒有意識到大社會所應擔負的歷史責任。總之,任何重大或前衛立法難
免會遇到一些麻煩,從族群正義的角度觀之,大社會的責任不在於指出麻煩然後拒絕原
住民族訴求,而難於解決麻煩促進族群平等地位。
二、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的操作性問題
從集體權的操作層面來看,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Lin(2007)指出,《條例》本身設置了一套專用權註冊制度,亦即第五條指出的「主管單
位得遴聘(派)有關機關人員、專家學者及原住民代表,辦理智慧創作之認定及其它法令
規定事項,其中原住民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但該文指出,此一制度困難重重。由
該文論述來看,一旦此一制度遭遇部落或原住民族此類集體,至少會出現三項問題或麻
煩,簡單臚列如下:
第一,《條例》以民族或部落為創作持有者以及權利被賦予單位,並由其承受可能
利益,但是 Lin(2007)指出,在台灣原住民族各族間,文化資訊(cultural information)的跨
界流動,在相互間貿易、遷居、爭戰的長遠歷史中,本來就是一種常態。在此一前提下,
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的賦予方式,會造成兩個問題:首先,某些傳統智慧創作明顯在各
族間流動,究竟應將權利歸屬哪一個民族,會引發爭議,譬如菱形圖案被泰雅族、排灣
族與魯凱族廣泛應用,布農族編織也常常融入鄰近部落居民創作意象。在此現實狀況
下,文化表現的所有權應該判分給誰,根本難以決定。其次,在此一文化資訊跨界流動
事實下,將智慧財產權賦予單一社群,形同「人為凍結文化間的界線,在相關人群與社
群間造成不平等。」(198)作者似乎認為,由於《條例》的集體權運作方式,是將其賦予
特定部落或民族,在族與族之間劃定了界線,讓某些原來在各族間流通並為大家所共同
使用的智慧創作權利,被侷限在特定部落或民族手中,最終使得可能也可以使用該創造
謀生的其它民族,因無法使用而致蒙受其害。
第二,《條例》以民族或部落為權利擁有單位,而非如同目前法律體系以個人為權
利擁有者,此一趨向本來就已在台灣法界引起疑慮。Lin(2007)更具體指出,在目前台灣
法律體系中,部落根本是「一個法律上模糊不清的實體(a legally vague entity),而且除非
先取得其所有成員的同意,否則不能行使任何法律權利。同時由於目前原住民族人口流
動與散佈模式,這也不可能取得。因此,若要實現此一立法的所有法律利益,會出現麻
煩。」(200)作者的意思似乎可以詮釋為兩個側面:首先,部落在台灣法律體系中是個含
混不清的概念,不像村里鄰在《地方制度法》中有明確的定位與職權,所以它如何有資
格成為專有權申請人,是大有問題的;其次,就算所謂的部落可以以接受成員同意委託
的方式代為主張某些權利,但目前原住民族人口的流動遷居狀況,根本不可能讓所謂的
部落成員行使此一同意權。
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