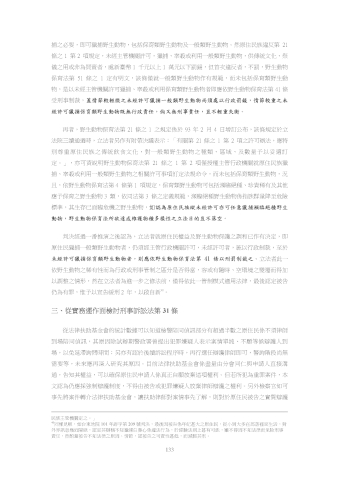Page 137 - 第四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137
捕之必要,即可獵捕野生動物,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及一般類野生動物。然原住民族違反第 21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物,供傳統文化、祭
儀之用或非為買賣者,處新臺幣 1 千元以上 1 萬元以下罰鍰,但首次違反者,不罰,野生動物
保育法第 51 條之 1 定有明文,該條僅就一般類野生動物作有規範,而未包括保育類野生動
物,是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者即應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1 條
受刑事制裁,蓋情節較輕微之未經許可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尚須處以行政罰鍰,情節較重之未
經許可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既無行政責任,倘又無刑事責任,豈不輕重失衡。
再者,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之規定係於 93 年 2 月 4 日增訂公布,該條規定於立
法院三讀通過時,立法者另作有附帶決議表示:「有關第 21 條之 1 第 2 項之許可辦法,應特
別尊重原住民族之傳統飲食文化,對一般類野生動物之種類、區域、及數量予以妥適訂
定。」,亦可資說明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第 2 項僅授權主管行政機關就原住民族獵
捕、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物之相關許可事項訂定法規命令,而未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況
且,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保育類野生動物可包括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其他
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3 類,依同法第 3 條之定義規範,瀕臨絕種野生動物係指族群量降至危險
標準,其生存已面臨危機之野生動物,如認為原住民族縱未經許可亦可任意獵捕瀕臨絕種野生
動物,野生動物保育法所欲達成維護物種多樣性之立法目的豈不落空。
判決經過一番推演之後認為,立法者就原住民權益及野生動物保護之調和已作有決定,即
原住民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者,仍須經主管行政機關許可,未經許可者,施以行政制裁,至於
未經許可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者,則應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1 條以刑罰制裁之。立法者此一
依野生動物之稀有性而為行政或刑事管制之區分是否得當,容或有隨時、空環境之變遷而得加
以調整之情形,然在立法者為進一步之修法前,僅得依此一管制模式適用法律,最後認定被告
40
仍為有罪,惟予以宣告緩刑 2 年,以啟自新 。
三、從實務運作面檢討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
從法律扶助基金會的統計數據可以知道檢警陪同偵訊部分有超過半數之原住民係不須律師
到場陪同偵訊,其原因除試辦期警政署曾提出犯罪嫌疑人表示案情單純、不願等候辯護人到
場,以免延滯詢問時間;另亦有認於後續訴訟程序時,再行選任辯護律師即可,警詢階段尚無
需要等,未來應再深入研究其原因。目前法律扶助基金會係盡量由分會同仁與申請人直接溝
通,告知其權益,可以確保原住民申請人係真正自願放棄這項權利。但若所犯為重罪案件,本
文認為仍應採強制辯護制度,不得由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放棄律師辯護之權利。另外檢察官如可
事先將案件轉介法律扶助基金會,讓扶助律師對案情事先了解,則對於原住民被告之實質辯護
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40 同樣見解,如台東地院 101 年訴字第 209 號判決,最後因被告係年紀甚大之原住民,從小到大多在部落裡面生活,對
外界訊息幾近隔絕,認定其辯稱不知獵捕白鼻心係違法行為,於經驗法則上甚有可能,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
責任,然酌量被告不知法律之原因、情節,認被告之可責性甚低,而減輕其刑。
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