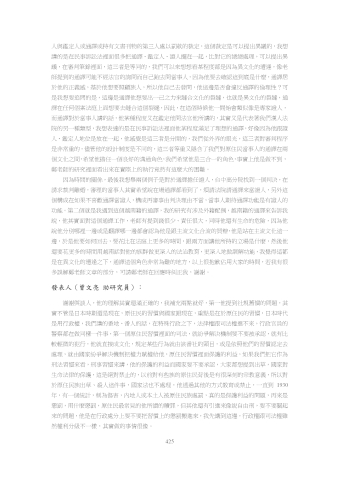Page 429 - 第四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429
人與鑑定人或通譯或持有文書刊物的第三人處以罰款的裁定,這個裁定是可以提出異議的,我想
講的是在民事訴訟法裡面很多把通譯、鑑定人、證人擺在一起,比對它的總總處理,可以提出異
議,在審判筆錄裡面,這三者是等同的,我們可以來想想看某程度都是因為異文化的遭逢,像老
師提到的通譯可能不經法官的詢問而自己跑去問當事人,因為他要去確認這到底是什麼,通譯居
於他的正義感,基於他想要照顧族人,所以他自己去發問,他這邊是否會違反通譯的倫理性?可
是我想要追問的是,這邊是通譯他想要出一己之力來縫合文化的裂縫,也就是異文化的裂縫,通
譯在任何個案法庭上面想要去縫合這個裂縫,因此,在這個時候他一開始會類似像是專家證人,
而通譯對於當事人講的話,他某種程度又在鑑定他問法官他所講的,其實又是代表著我們漢人法
院的另一種類型,我想表達的是在民事訴訟法裡面他某程度滿足了理想的通譯,好像因為他跟證
人、鑑定人地位是放在一起,他感覺是這三者是分開的,我們從外界的眼光,這三者對審判程序
是非常重的,儘管他的設計制度是不同的,這三者等重又隱含了我們對原住民當事人的通譯在兩
個文化之間,希望他擔任一個良好的溝通角色,我們希望他是三合一的角色,事實上他是做不到,
鄭老師的研究裡面看出來在實際上的執行竟然有這麼大的困難。
因為時間的關係,最後我想舉兩個例子是對於通譯擔任證人,台中高分院找到一個判決,在
請求裁判離婚,審理的當事人其實希望說在場通譯都看到了,煩請法院請通譯來當證人,另外這
個構成在如果不喜歡通譯當證人,構成再審事由判決理由不當,當事人期待通譯功能是有證人的
功能。第二個就是我遇到這個越南籍的通譯,我的研究有涉及外籍配偶,越南籍的通譯來告訴我
說,他其實面對這個通譯工作,老師有提到錢很少、責任很大,同時他還有生命的危險,因為他
說他分別哪裡一邊或是翻譯哪一邊都會認為他是跟主流文化合流的買辦,他是站在主流文化這一
邊,於是他要如何回去,要花比在法庭上更多的時間,跟兩方面講他所持的立場是什麼,然後他
還要花更多的時間用越南話對他的族群做更深入的法治教育,更深入地做調解功能,我覺得這都
是在異文化的遭逢之下,通譯這個角色非常為難的地方,以上很抱歉佔用大家的時間,若我有很
多誤解鄭老師文章的部分,可請鄭老師在回應時糾正我,謝謝。
發表人(曾文亮 助研究員):
謝謝與談人,他的理解其實還滿正確的,我補充兩點就好,第一他提到社規舊慣的問題,其
實不管是日本時期還是現在,原住民的習慣與國家跟現在,重點是在於原住民的習慣,日本時代
是用行政權,我們講的番地、番人的話,在特殊行政之下,法律權跟司法權進不來,行政官員的
警察都在做同樣一件事,第一個原住民習慣裡面的司法,就紛爭解決機制要不要被承認,就有比
較輕微的犯行,他就直接成文化,規定某些行為就由該番社的頭目,或是依照他們的習慣認定去
處理,就由國家紛爭解決機制把權力賦權給他,原住民習慣裡面保護的利益,如果我們把它作為
刑法習慣來看,刑事習慣來講,他的保護的利益而國家要不要承認,大家都想提到出草,國家對
生命法律的保護,這是絕對禁止的,以前對有些族的原住民背後是有很深刻的宗教意義,所以對
於原住民族出草、殺人這件事,國家法也不處理,他透過其他的方式教育或禁止,一直到 1930
年,有一個統計,稱為傷害,內地人或本土人被原住民族處罰,真的是保護利益的問題,再來是
懲罰,用什麼懲罰,原住民最常見的他所謂的贖罪,但其他還有引進來像說自由刑,要不要關起
來的問題,他是在行政處分上要不要把習慣上的懲罰搬進來,我先講到這邊,行政權跟司法權雖
然權利分級不一樣,其實做的事情很像。
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