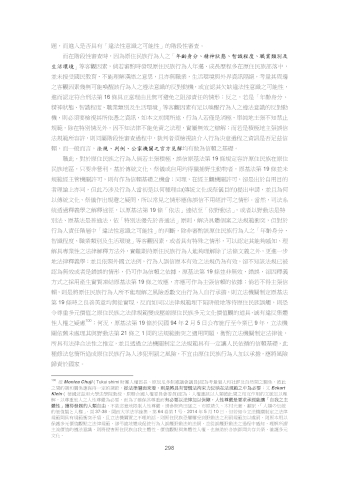Page 302 - 第五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302
題,而進入是否具有「違法性意識之可能性」的階段性審查。
而在階段性審查時,因為原住民族行為人之「年齡身分、精神狀態、智識程度、職業類別及
生活環境」等客觀因素,倘若審酌時發現原住民族行為人年邁、成長歷程多在原住民族部落中,
並未接受國民教育、不能理解漢語之意思,且亦無職業,生活環境與外界資訊隔絕,考量其周邊
之客觀因素幾無可能喚醒該行為人之遵法意識的反對動機,或宜認其欠缺違法性意識之可能性,
進而認定符合刑法第 16 條具正當理由且無可避免之阻卻責任的情形;反之,若是「年齡身分、
精神狀態、智識程度、職業類別及生活環境」等客觀因素有足以喚醒行為人之遵法意識的反對動
機,則必須要檢視其所依憑之資訊,如本文前開所述,行為人若僅是消極、單純地主張不知禁止
規範,除在特別情況外,因不知法律不能免責之法理,實屬無效之辯解;而若是積極地主張誤信
法規範所容許,則同屬階段性審查過程中,裁判者須檢視該介入行為決意過程之資訊是否足茲信
賴,而一般而言,法規、判例、公家機關之官方見解均有做為信賴之基礎。
職此,對於原住民族之行為人倘若主張積極、誤信原基法第 19 條規定容許原住民族在原住
民族地區,只要非營利,基於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均得獵捕野生動物者,原基法第 19 條並未
規範經主管機關許可,則有作為信賴基礎之機會;同理,在經主觀機關許可,卻是出於自用目的
者理論上亦同,但此乃涉及行為人當初是以何種理由(傳統文化或祭儀目的)提出申請,並且為何
以傳統文化、祭儀作出規避之疑問,所以常見之情形應係誤信不用經許可之情形。當然,司法系
統透過釋義學之解釋途徑,以原基法第 19 條「依法」連結至「依野動法」,或者以野動法是特
別法、原基法是普通法,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原則,解決具體個案之法規範衝突,但對於
行為人責任階層中「違法性意識之可能性」的判斷,除非審酌該原住民族行為人之「年齡身分、
智識程度、職業類別及生活環境」等客觀因素,或者具有特殊之情形,可以認定其能夠感知、理
解具專業性之法律解釋方法外,實難期待原住民族行為人能夠理解除了法條文義之外,更進一步
地法律釋義學;並且依照外國立法例,行為人誤信原本有效之法規仍為有效,卻不知該法規已被
認為無效或者是錯誤的情形,仍可作為信賴之依據,原基法第 19 條並非無效、錯誤,卻因釋義
方式之採用產生實質凍結原基法第 19 條之效應,亦應可作為主張信賴的依據;倘若不得主張信
賴,則是將原住民族行為人所不能理解之風險悉數交由行為人自行承擔,則立法機關制定原基法
第 19 條時之良善美意均無從實現,反而如同以法律規範埋下陷阱般地等待原住民族誤觸,則恐
令尊重多元價值之原住民族之法律規範變成壓縮原住民族多元文化價值觀的道具,誠有違反集體
性人權之疑慮 100 ;何況,原基法第 19 條於民國 94 年 2 月 5 日公布施行至今業已 9 年,立法機
關依舊未處理其與野動法第 21 條之 1 間的法規範衝突之適用問題,衡酌立法機關制定法律後,
所具有法律合法性之推定,並且透過立法機關制定之法規範具有一定讓人民依循的信賴基礎,此
種修法怠惰所造成原住民族行為人涉犯刑罰之風險,不宜由原住民族行為人加以承擔,應將風險
歸責於國家。
100
按 Monica Chuji ( Tukui shimi 財團人權部長、原厄瓜多制憲議會議員)認為考量個人和社群及自然間之關係,彼此
之間的調和關係應保持一定的調節,從法律層面來看,則是將具有習慣法拘束力反映在法規範之中為必要;又 Eckart
Klein ( 德國波茲坦大學法學院教授、原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委員)認為:人權應該以人類彼此間之相互作用的文脈加以理
解,以尊重他人之人性尊嚴為必要,而為了確保其尊重而有必要以法律加以保障,人性尊嚴是要求承認能讓「自我之主
體性」獲得發展的人類自由,不能恣意地限制人性尊嚴。請參照角田猛之、市原靖久、木村光豪,翻訳,「人類の伝統
的価值観と人権」,頁 37-38,関西大学法学論集,第 64 卷第 1 号,2014 年 5 月 10 日。但若如今立法機關制定之法律
規範間具有規範衝突矛盾,且立法機關置之不理的話,則原住民族恐屢屢受到野動法之刑罰規範加以處罰,則原本用以
保護多元價值觀點之法律規範,卻弔詭地變成促使行為人誤觸野動法的法網,並從誤觸野動法之過程中感知、理解所謂
主流價值的遵法意識,則將侵害原住民族自我主體性、價值觀點與集體性人權,也無助於各族群間共存共榮、維護多元
文化。
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