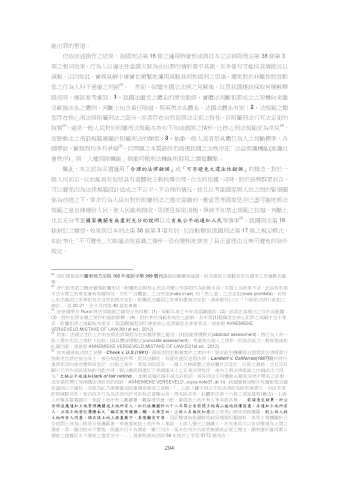Page 298 - 第五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298
能出罪的管道。
但依前述操作之結果,我國刑法第 16 條之運用將會形成與日本立法例即刑法第 38 條第 3
項之相同效果,行為人以違法性意識欠缺為由出罪的情形微乎其微,至多僅有可能按其情節加以
減輕,正因如此,實務見解中確實也頻繁地運用減輕其刑和緩刑之思維,避免對於非難性程度較
92
低之行為人科予過重之刑罰 。 然而,綜覽外國立法例之見解後,反思我國應該採取何種解釋
路徑時,應該要考慮到:○ 1、我國法繼受之體系的歷史脈絡,實體法判斷犯罪成立之架構向來繼
受歐陸法系之體例,判斷上包含責任階層,與英美法系體系、法國法體系有別;○ 2、法規範之類
型存在核心刑法與附屬刑法之區分,前者存在自然犯與法定犯之特性,但附屬刑法只有法定犯的
94
93
特質 ,通常一般人民對於附屬刑法規範本身有不知或錯誤之情形,比核心刑法規範更為常見 ,
而野動法之刑罰規範應屬於附屬刑法的類型;○ 3、抽象一般人或者是具體行為人之判斷標準,各
95
國學說、實務間均多有爭辯 ,但問題之本質最終仍端視我國之法秩序在「法益保護機能(維護社
會秩序)」與「人權保障機能」側重何種刑法機能所展現之價值觀點。
職此,本文認為妥適運用「合理的法律錯誤」或「可否避免之違法性錯誤」的概念,對於一
般人民而言,反而能具有促使其有意願地主動找尋合理、合法的依據,同時,對於弱勢群眾而言,
可以避免因為法律規範設計造成之不公平、不合理的情況,並且以考量國家與人民之間的緊張關
係為前提之下,要求行為人具有對於附屬刑法之遵法意識前,應當思考國家是否已盡可能地將法
規範之意旨傳遞給人民,使人民能夠接收,即便是採取消極、單純不知禁止規範之抗辯,判斷上
96
也宜充分考量國家機關有無盡到充分的說明以及有無公平地通知人民等情事 ,我國刑法第 16
條制訂之類型、效果與日本刑法第 38 條第 3 項有別,反而較類似德國刑法第 17 條之規定模式,
如此窄化「不可避免」欠缺違法性意識之情形,恐有變相地架空了具正當理由且無可避免的除外
規定。
92
按即便是如同臺東地方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209 號判決鉅細靡遺地論證,終究僅能以減輕其刑及緩刑之思維模式處
理。
93
按行政刑罰之概念實係附屬刑法,附屬刑法與核心刑法同樣以刑事罰作為制裁手段,本質上為刑事不法,而具有刑事
不法本質之刑事犯兼有兩種特性,亦即「自體惡」之自然犯(mala in se) 和「禁止惡」之法定犯(mala prohibita),而核
心刑法處罰之刑事犯包含自然犯與法定犯,附屬刑法處罰之刑事犯僅有法定犯。請參照林山田,「行政刑法與行政犯之
辯正」,頁 20-21,法令月刊第 40 卷第 9 期。
94
按德國學者 Roxin 將法律錯誤之類型分為四種:(1)、規範本身之不知或認識錯誤;(2)、誤認正當理由之存在或範圍;
(3)、對於犯罪定義之要件的錯誤解釋;(4)、對於某些規範有效性之誤解。其中第(1)種類型在核心犯罪之規範中並不常
見,附屬犯罪之規範較為常見;第(2)種類型則即便是核心犯罪類型也非常常見。請參照 ANNEMIEKE
VERSEVELD,MISTAKE OF LAW,36(1st ed., 2012).
95
例如:法國立法例上亦有依照犯罪類型存在兩種評價之區別:(1)抽象評價模式(abstract assessment):將行為人和一
般人置於相同之情狀下比較;(2)具體評價模式(concrete assessment):考慮被告個人之情形,例如其能力、教育等諸如
此類因素。請參照 ANNEMIEKE VERSEVELD,MISTAKE OF LAW,52(1st ed., 2012).
96
按美國最高法院之見解,Cheek v. U.S.(1991),最高法院在稅務案件之案件中:要求政府機關要去證明該法律將責任
強制地加諸在被告身上,被告知道這件事,而其自願地、有意地違反這個法律;Lambert v. California(1957)關於前科
重罪犯須向當地警察局登記、註冊之案件,最高法院認為:一個人欠缺確實之認知關於其登記、註冊之義務,並且沒有
顯示任何作成該認知的可能性時,與以處罰則違反了美國憲法上之正當法律程序。被告主張法律錯誤之抗辯成功乃因
為「欠缺公平地通知(lack of fair notice)」,如果這個抗辯不被允許的話,被告則沒任何機會去避免法律所帶來之結果,
或者是防禦任何伴隨法律而來的控訴。ANNEMIEKE VERSEVELD, supra note37, at 14. 我國實務見解亦有類似要求國
家盡到公平通知,並認為此乃事實審法院應調查事項之見解:「…上訴人雖不得以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
節得減輕其刑;如自信其行為為法律所許可而有正當理由者,得免除其刑,此觀刑法第十六條之規定甚明(舊法)。上訴
人所稱其搭蓋廟宇,係經土地所有人戴蕃薯、戴春塗同意一節,業經該土地所有人等承認其事。…前項查定結果,於公
告時並應通知土地管理機關或土地所有人。如行政機關於六十八年間公告前開土地為山坡地保護區後,未通知土地所有
人,且該土地登記簿謄本之「編定使用種類」欄,又係空白,上訴人自無從知悉該土地係山坡地或保護區,則上訴人經
土地所有人同意,誤在該土地上搭蓋廟宇,其情顯有可原,因而聲請向桃園縣地政局調閱相關資料,查明主管機關於公
告前開土地為山坡地及保護區後,有無通知該土地所有人等語。上訴人選任之辯護人,亦先後兩次以言詞聲請為上開之
調查。第一審法院未予置理,原審亦仍不為調查,遽行判決,復未在判決內說明無調查必要之理由,顯有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請參照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5172 號判決。
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