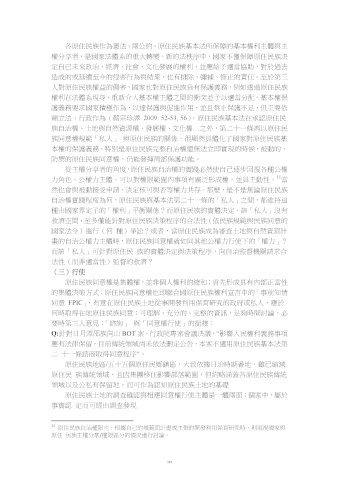Page 363 - 第六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363
各原住民族作為憲法、兩公約、原住民族基本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主體與主
權分享者,是國家法體系的重大轉變。新的法秩序中,國家不僅保障原住民族決
定自己未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權利,並應給予適當協助,對於過去
造成的或延續至今的侵害行為與結果,也有排除、彌補、修正的責任。至於第三
人對原住民族權益的傷害,國家也對原住民族負有保護義務,例如透過原住民族
權利在法體系現身,重新介入基本權主體之間的衝突並予以適當分配。基本權保
護義務要求國家積極作為,以達保護與促進作用,並且禁止保護不足,但主要依
賴立法、行政作為(蔡宗珍譯 2009: 52-53, 56)。原住民族基本法在承認原住民
族自治權、土地與自然資源權、發展權、文化權…之外,第二十一條再以原住民
族同意權規範「私人」 與原住民族的關係,很顯然具體化了國家對原住民族基
本權的保護義務。特別是原住民族完整自治權還無法立即實現的時候,被動的、
防禦的原住民族同意權,仍能發揮局部保護功能。
從主權分享者的角度,原住民族自治權的實踐必然使自己逐步回復各種公權
11
力角色。公權力主體,可以對權限範圍內事項有廣泛形成權,並具主動性, 當
然也會與被動接受申請、決定核可與否等權力共存。那麼,是不是無論原住民族
自治權實踐程度為何,原住民族與基本法第二十一條的「私人」之間,都維持這
種由國家界定了的「權利」平衡關係?而原住民族的實體決定,該「私人」沒有
救濟空間,至多僅能針對原住民族決策程序的合法性(依民族規範與民族同意的
國家法令)進行(何 種)爭訟?或者,當原住民族成為審查土地與自然資源計
畫的自治公權力主體時,原住民族同意權就如同其他公權力行使下的「權力」?
而該「私人」可針對原住民 族的實體決定與決策程序,向自治監督機關請求合
法性(而非適當性)監督的救濟?
(三)行使
原住民族同意權是集體權,並非個人權利的總和;首先形成具有內部正當性
的集體決策方式;原住民族同意權也即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中的「事前知情
同意 FPIC」,有意在原住民族土地從事開發利用保育研究的政府或私人,應於
何時取得在地原住民族同意;可理解、充分的、完整的資訊,足夠時間討論、必
要時第三人意見;「諮詢」 與「同意權行使」的銜接;
Q:針對日月潭邵族向山 BOT 案,行政院專案會議決議,“影響人民權利義務事項
應有法律保留,目前傳統領域尚未依法劃定公告,本案不適用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二 十一條諮商取得同意程序“。
原住民族地區/五十五個原住民鄉鎮區,大致依據日治時期番地,雖已縮減
原住民 族傳統領域,且因集團移住影響部落範圍,但約略涵蓋各原住民族傳統
領域以及公私有保留地,而可作為認知原住民族土地的基礎
原住民族土地的調查確認與相應同意權行使主體是一體兩面;個案中,屬於
事實認 定而可經由調查發現
11
原住民族自治權限內,根據自己的規範而計畫或主張的開發利用保育研究時,則須視國家與
原住 民族主權分享/權限區分的情況進行討論。
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