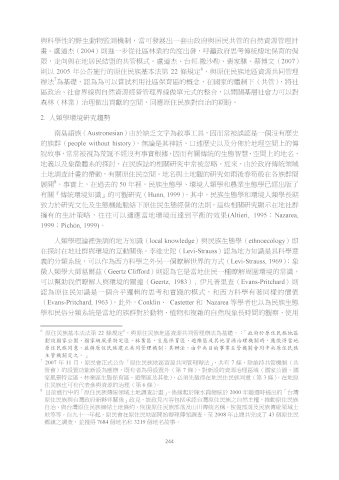Page 248 - 第一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248
與科學性的野生動物監測機制,當可發展出一套由政府與居民共管的自然資源管理計
畫。盧道杰(2004)則進一步從社區林業的角度出發,呼籲政府思考傳統棲地保育的侷
限,走向與在地居民結盟的共管模式。盧道杰、台邦.撒沙勒、裴家騏、蔡博文(2007)
6
則以 2005 年公告施行的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2 條規定 ,與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
7
辦法 為基礎,認為為可以嘗試利用社區保育區的概念,在國家的體制下(共管),將社
區政治、社會界線與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界線做單元式的整合,以開闢基層社會力可以對
森林(林業)治理做出貢獻的空間,回應原住民族對自治的期盼。
2. 人類學環境研究趨勢
南島語族(Austronesian)由於缺乏文字為敘事工具,因而常被誤認是一個沒有歷史
的族群(people without history),無論是其神話、口述歷史以及分佈於地理空間上的傳
說故事,常常被視為荒誕不經沒有事實根據,因而有關傳統的生態智慧、空間上的地名、
地義以及象徵體系的探討,在民族誌的相關研究中常被忽略。近來,由於政府傳統領域
土地調查計畫的帶動,有關原住民空間、地名與土地觀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在各族群間
8
展開 。事實上,在過去的 50 年裡,民族生態學、環境人類學和農業生態學已經出版了
有關『傳統環境知識』的可觀研究(Hunn, 1999),其中,民族生態學和環境人類學長期
致力於研究文化及生態機能脈絡下原住民生態經營的法則,這些相關研究顯示在地社群
擁有的生計策略,往往可以適應當地環境而達到平衡的效果(Altieri, 1995;Nazarea,
1999;Pichón, 1999)。
人類學理論裡強調的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與民族生態學(ethnoecology)即
在探討在地社群與環境的互動關係。李維史陀(Levi-Strauss)認為地方知識是具科學意
義的分類系統,可以作為西方科學之外另一個瞭解世界的方式(Levi-Strauss, 1969);象
徵人類學大師葛爾茲(Geertz Clifford)則認為它是當地住民一種瞭解周圍環境的常識,
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人與環境的關連(Geertz, 1983); 伊凡普里查(Evans-Pritchard)則
認為原住民知識是一個合乎邏輯的思考和實踐的模式,和西方科學有著同樣的價值
(Evans-Pritchard, 1963)。此外,Conklin、 Castetter 和 Nazarea 等學者也以為民族生態
學和民俗分類系統是當地的族群對於動物、植物和複雜的自然現象長時間的觀察、使用
6
6 原住民族基本法法第 22 條規定 ,與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為基礎,:「政府於原住民族地區
劃設國家公園、國家級風景特定區、林業區、生態保育區、遊樂區及其他資源治理機關時,應徵得當地
原住民族同意,並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其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定之。」
7 2007 年 11 月,原民會正式公告「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共有 7 條,除維持共管機制(共
管會)的設置功能新設為應辦,既有者為得設置外(第 7 條),對新設的資源治理區域(國家公園、國
家風景特定區、林業區生態保育區、遊樂區及其他),必須先徵得在地民住民族同意(第 3 條),在地原
住民族也可有代表參與資源的治理(第 6 條)。
8 目前進行中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計畫」,係緣起於陳水扁總統於 2000 年競選時提出的「台灣
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夥伴關係」政見,該政見內容包括承認台灣原住民族之自然主權、推動原住民族
自治、與台灣原住民族締結土地條約、恢復原住民族部落及山川傳統名稱、恢復部落及民族傳統領域土
地等等。自九十一年起,原民會在原住民地區開始辦理傳領調查,至 2008 年止總共完成了 43 個原住民
鄉鎮之調查,並獲得 7684 個地名和 3219 個地名故事。
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