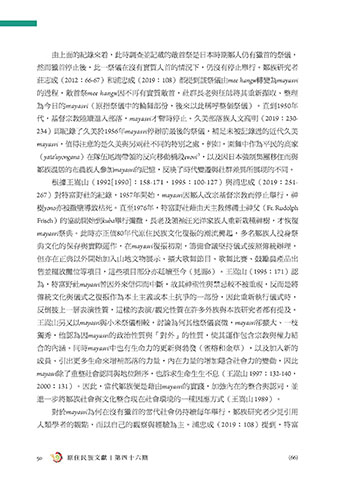Page 66 - 原住民族文獻第10輯
P. 66
由上面的紀錄來看,此時調查並記載的敵首祭是日本時期鄒人仍有獵首的祭儀,
然而獵首停止後,此一祭儀在沒有實質人首的情況下,仍沒有停止舉行。鄒族研究者
莊志成(2012:66-67)和浦忠成(2019:108)都提到該祭儀由mee hangʉ轉變為mayasvi
的過程,敵首祭mee hangʉ因不再有實質敵首,社群長老與征帥將其重新擷取、整理
為今日的mayasvi(原指祭儀中的輪舞部份,後來以此稱呼整個祭儀)。直到1950年
代,基督宗教陸續進入部落,mayasvi才暫時停止。久美部落族人文高明(2019:230-
234)即紀錄了久美於1956年mayasvi停辦前最後的祭儀,補足未被記錄過的近代久美
mayasvi,值得注意的是久美與另兩社不同的特別之處,例如,圍舞中作為平民的高家
3
(yata’uyongana)在隊伍尾端帶領的反向移動橋段evovi ,以及因日本強制集團移住而與
鄒族混居的布農族人參加mayasvi的記憶,反映了時代變遷與社群差異所展現的不同。
根據王嵩山(1992[1990]:158-171,1995:100-127)與浦忠成(2019:251-
267)對特富野社的紀錄,1957年開始,mayasvi因鄒人改宗基督宗教而停止舉行,神
樹yono亦被撒鹽導致枯死。直至1976年,特富野社藉由天主教傅禮士神父(Fr. Rudolph
Frisch)的協助開始到kuba舉行彌撒,長老及領袖汪光洋家族人重新栽種神樹,才恢復
mayasvi祭典。此時亦正值80年代原住民族文化復振的潮流興起,多名鄒族人投身祭
典文化的保存與實際運作,在mayasvi復振初期,籌備會議堅持儀式按照傳統辦理,
但亦在正典以外開始加入山地文物展示、擴大歌舞節目、歌舞比賽、鼓勵農產品出
售並擺放攤位等項目,這些項目部分亦延續至今(見圖6)。王嵩山(1995:171)認
為,特富野社mayasvi曾因外來信仰而中斷,故其神聖性與禁忌較不被重視,反而是將
傳統文化與儀式之復振作為本土主義或本土抗爭的一部份,因此重新執行儀式時,
反倒披上一層表演性質,這樣的表演/觀光性質在許多外族與本族研究者都有提及。
王嵩山另又以mayasvi與小米祭儀相較,討論為何其他祭儀衰微,mayasvi卻擴大、一枝
獨秀,他認為因mayasvi的政治性質與「對外」的性質,使其運作包含宗教與權力結
合的內涵。同時mayasvi中也有生命力的更新與勃發(雀榕和金草),以及加入新的
成員、引出更多生命來增補部落的力量,內在力量的增加隱含社會力的變動,因此
mayasvi除了重整社會認同與地位階序,也訴求生命生生不息(王嵩山 1997:132-140,
2000:131)。因此,當代鄒族便是藉由mayasvi的實踐,加強內在的整合與認同,並
進一步將鄒族社會與文化整合現在社會環境的一種因應方式(王嵩山 1989)。
對於mayasvi為何在沒有獵首的當代社會仍持續每年舉行,鄒族研究者少見引用
人類學者的觀點,而以自己的觀察與經驗為主。浦忠成(2019:108)提到,特富
50 原 住 民 族 文 獻 | 第 四 十 六 期 (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