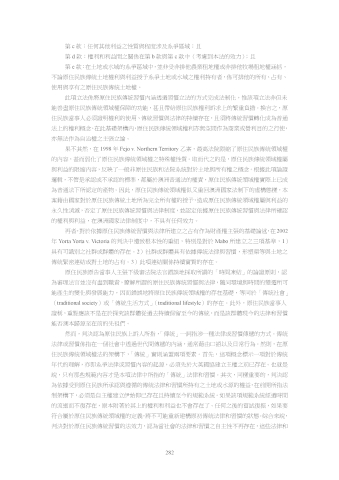Page 286 - 第四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286
第 c 款:任何其他利益之性質與程度涉及系爭區域;且
第 d 款:權利和利益間之關係在第 b 款與第 c 款中(考慮到本法的效力);且
第 e 款 : 在 土地或水域的系爭區域中,並非受非排他農業租地權或非排他牧場租地權涵括,
不論原住民族傳統土地權利與利益授予系爭土地或水域之權利持有者,係可排他的所有、占有、
使用與享有之原住民族傳統土地權。
此項立法係將原住民族傳統習慣內涵透過習慣立法的方式完成法制化,惟該項立法非但未
能善盡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保障的功能,甚且帶給原住民族權利訴求上的繁重負擔。換言之,原
住民族當事人必須證明權利的使用、傳統習慣與法律的持續存在,且須將傳統習慣轉化成為普通
法上的權利概念。在此基礎架構內,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利亦無空間作為商業或營利目的之行使,
亦無法作為自治權之主張立論。
果不其然,在 1998 年 Fejo v. Northern Territory 乙案,最高法院限縮了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
的內容,甚而弱化了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之特殊權性質。取而代之的是,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屬
與利益的限縮內容,反映了一般非原住民族和法院系統對於土地與所有權之概念。根據此項論證
邏輯,不管是承認或不承認的標準,都屬於澳洲普通法的權責,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實際上已成
為普通法下所認定的產物。因此,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似又重回澳洲國家法制下的虛構態樣,本
案藉由國家對於原住民族傳統土地所為完全所有權的授予,造成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屬與利益的
永久性消滅,否定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與法律制度,並認定依據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與法律所確認
的權利與利益,在澳洲國家法律制度中,不具有任何效力。
再者,對於依據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與法律所建立之占有作為財產權主張的基礎論述,在2002
年 Yorta Yorta v. Victoria 的判決中遭致根本性的重組,特別是對於 Mabo 所建立之三項基準,1)
具有可識別之社群或群體的存在。2)社群或群體具有依據傳統法律與習慣,形塑渠等與土地之
傳統緊密連結或對土地的占有。3)此項連結關係持續實質的存在。
原住民族原告當事人主張下級審法院法官錯誤地採取所謂的「時間凍結」的論證原則,認
為審理法官並沒有盡到職責,瞭解所謂的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與法律,隨同環境與時間的變遷所可
能產生的變化與發展能力,因而錯誤地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的存在基礎,等同於「傳統社會」
(traditional society)或「傳統生活方式」(traditional lifestyle)的存在。此外,原住民族當事人
證稱,重點應該不是在於探究該群體從過去持續保留至今的傳統,而是該群體現今的法律和習慣
能否溯本歸源至在前的先祖們。
然而,判決認為原住民族上訴人所指,「傳統」一詞指涉一種法律或習慣傳遞的方式。傳統
法律或習慣係指在一個社會中透過世代間傳遞的內涵,通常藉由口語以及日常行為。然則,在原
住民族傳統領域權法的架構下,「傳統」實則涵蓋兩項要素。首先,這項概念標示一項對於傳統
年代的理解,亦即系爭法律或習慣內容的起源,必須先於大英國協建立主權之前已存在。也就是
說,只有那些規範內容才是本項法律中所指的「傳統」法律和習慣。其次,同樣重要的,判決認
為依據受到原住民族所承認與遵循的傳統法律和習慣所持有之土地或水源的權益,在前開所指法
制架構下,必須是自主權建立伊始即已存在且持續至今的規範系統。如果該項規範系統經過時間
的流逝而不復存在,原本附著於其上的權利和利益也不會存在了。任何之後的嘗試復振,如果要
符合屬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的定義,將不可能重新建構原初傳統法律和習慣的狀態。綜合來說,
判決對於原住民族傳統習慣的法效力,認為當社會的法律和習慣之自主性不再存在,這些法律和
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