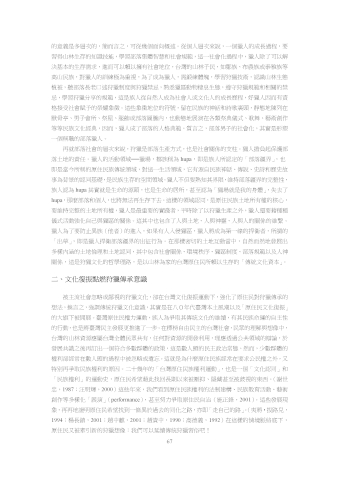Page 71 - 第四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71
的意義是多層次的,簡而言之,可從幾個面向概述。從個人層次來說,一個獵人的成長過程,要
習得山林生存的知識技能,學習部落集體智慧和社會規範,這一社會化過程中,獵人除了可以解
決基本的生存需求,進而可以賴以擁有社會地位,台灣的山林子民,如鄒族、布農族或泰雅族等
高山民族,對獵人的訓練極為重視,為了成為獵人,需鍛練體魄,學習狩獵技術,認識山林生態
植被,聽部落長老口述狩獵制度與狩獵禁忌,熟悉獵區動物棲息生態,遵守狩獵規範和相關的禁
忌,學習狩獵分享的規範,這是族人從自然人成為社會人或文化人的成長歷程,好獵人因而有資
格接受社會賦予的榮耀象徵。這些象徵地位的符號,留在民族的神話和詩歌裏頭,靜態地陳列在
獸骨亭、男子會所、祭屋、服飾或部落圖騰內,也動態地展演在各類祭典儀式、歌舞、藝術創作
等等民族文化經典,因而,獵人成了部落的人格典範。質言之,部落男子的社會化,其實是形塑
一個稱職的部落獵人。
再就部落社會的層次來說,狩獵是部落生產方式,也是社會關係的支柱。獵人擔負起保護部
落土地的責任。獵人的活動領域──獵場,鄒族稱為 hupa,即是族人所認定的「部落疆界」,也
即是當今所稱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對這一生活領域,它有源自民族神話、傳說、史詩和歷史故
事為背景的認同基礎,是民族生存的空間領域。獵人不但要熟知其界限,維持部落疆界的完整性,
族人認為 hupa 其實就是生命的源頭,也是生命的居所,甚至認為「獵場就是我的身體」,失去了
hupa,那麼部落和個人,也將無法再生存下去。這樣的領域認同,是原住民族土地所有權的核心,
要維持完整的土地所有權,獵人是最重要的實踐者,平時除了以狩獵生產之外,獵人還要藉種種
儀式活動強化自己與獵區的關係。這其中也包含了人與土地、人與神靈、人與人的關係的維繫。
獵人為了要防止異族(他者)的進入,如果有人入侵獵區,獵人將成為第一線的捍衛者,所謂的
「出草」,即是獵人捍衛部落疆界的出征行為。在那樣密切的土地互動當中,自然而然地發展出
多樣內涵的土地倫理和土地認同,其中包含社會關係、環境秩序、獵區制度、部落規範以及人神
關係,這是狩獵文化的哲學理路,是以山林為家的台灣原住民所賴以生存的「傳統文化資本」。
二、文化復振點燃狩獵傳承意識
被主流社會忽略或鄙視的狩獵文化,卻在台灣文化復振運動下,強化了原住民對狩獵傳承的
想法,換言之,強調傳統狩獵文化意識,其實是在八0年代臺灣本土風潮以及「原住民文化復振」
的大旗下被開展。臺灣原住民權力運動,族人為爭取其傳統文化的維續,有其民族命運的自主性
的行動,也是將臺灣民主發展更推進了一步。在標榜自由民主的台灣社會,民眾的理解與想像中,
台灣的山林資源應屬台灣全體民眾共有,任何對資源的開發利用,理應透過公共領域的辯論,於
發展共識之後再訂出一個符合多數群體的政策,這是數人頭的民主政治常態。然而,少數群體的
權利卻經常在數人頭的過程中被忽略或遺忘。這就是為什麼原住民族經常在要求公民權之外,又
特別再爭取民族權利的原因。二十幾年的「台灣原住民族權利運動」,也是一個「文化認同」和
「民族權利」的運動史,原住民希望藉此找回長期以來被壓抑、隱藏甚至被歧視的東西。(謝世
忠,1987;汪明輝,2000)這些年來,我們看到原住民族權利的法制建構、民族教育活動、藝術
創作等多樣化「展演」(performance),甚至努力爭取原住民自治(施正鋒,2001)。這些發展現
象,再再地證明原住民希望找到一條異於過去的同化之路,亦即「走自己的路」。(夷將‧拔路兒,
1994;楊長鎮,2001;趙中麒,2001;趙貴中,1990;高德義,1992)在這樣的情境脈絡底下,
原住民又被牽引新的狩獵想像:我們可以延續傳統狩獵習俗吧!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