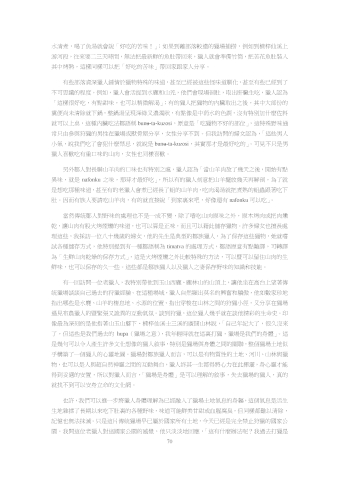Page 74 - 第四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74
水清煮,喝了魚湯就會說「好吃的苦味!」;如果到離部落較遠的獵場捕撈,例如到楠梓仙溪上
游河段,往來要二三天時間,無法把最新鮮的魚肚帶回來,獵人就會準備竹筒,把苦花魚肚裝入
其中烤熟,這樣同樣可以把「好吃的苦味」帶回家跟家人分享。
有些部落資深獵人鍾情於獵物特殊的味道,甚至已經被這些怪味道馴化,甚至有些已經到了
不可思議的程度。例如,獵人會活捉到水鹿和山羌,他們會現場剖肚,取出肝臟生吃,獵人認為
「這樣很好吃,有點甜味,也可以稍微解渴」;有的獵人把獵物的內臟取出之後,其中大部份的
糞便尚未清除就下鍋,整鍋湯呈現深綠又濃濁狀,有點像是中葯水的色調,沒有特別加什麼佐料
就可以上桌,這種內臟吃法鄒語稱 bunu-ta-kuzosi,原意是「吃獵物不好的部位」,這特殊野味通
常只由參與狩獵的男性在獵場或獸骨屋分享,女性分享不到。但我訪問的婦女認為,「這些男人
小氣,說我們吃了會犯什麼禁忌,就說是 bunu-ta-kuzosi,其實那才是最好吃的」。可見不只是男
獵人喜歡吃有重口味的山肉,女性也同樣喜歡。
另外鄒人對長鬃山羊肉的口味也有特別之處,獵人認為「當山羊肉放了幾天之後,開始有點
異味,就是 nafonku 之味,那時才最好吃」,所以有的獵人刻意把山羊擺放幾天再解剖,為了就
是想吃那種味道,甚至有的老獵人會煮已經長了蛆的山羊肉,吃肉渴湯就把煮熟的蛆蟲跟著吃下
肚。因而有族人要請吃山羊肉,有的就直接說「到家裏來吧,好像還有 nafonku 可以吃」。
當然傳統鄒人對野味的處理也不是一成不變,除了嗜吃山肉原味之外,原木烤肉或把肉爋
乾,讓山肉有股火烤煙爋的味道,也可以算是正味,而且可以藉此儲存獵物。許多婦女也擅長處
理這些,我採訪一位八十幾歲的婦女,他的先生是典型的鄒族獵人,為了保存這些獵物,她就嚐
試各種儲存方式,他特別提到有一種鄒語稱為 timatva 的處理方式,鄒語原意有點難譯,可轉譯
為「生鮮山肉乾燥的保存方式」,這是火烤煙爋之外比較特殊的方法,可以暨可以留住山肉的生
鮮味,也可以保存的久一些。這些都是鄒族獵人以及獵人之妻保存野味的知識和技能。
有一回訪問一位老獵人,我特別帶他到玉山西鹿、鹿林山的山頂上,讓他坐在高台上望著傳
統獵場談談自己過去的狩獵經驗。在這種場域,獵人自然顯出莫名的興奮和驕傲,他如數家珍地
指出哪些是水鹿、山羊的棲息地、水源的位置、指出穿梭在山林之間的狩獵小徑,又分享在獵場
遇見布農獵人的暨緊張又詭異的互動氣氛。談到狩獵,這位獵人幾乎就在談他精彩的生命史。印
像最為深刻的是他指著山玉山腳下、楠梓仙溪士三溪的廣闊山林說,「 自己年紀大了,很久沒來
了,但這些是我們過去的 hupa(獵場之意),我年輕時就在這裏打獵,獵場是我們的身體」。這
是幾句可以令人產生許多文化想像的獵人敘事,特別是獵場與身體之間的關聯,整個獵場土地似
乎構築了一個獵人的心靈地圖。獵場對鄒族獵人而言,可以是有物質性的土地、河川、山林與獵
物,也可以是人與超自然神靈之間的互動舞台,獵人終其一生都得將心力在此揮灑,身心靈才能
得到妥適的安置,所以對獵人而言,「獵場是身體」是可以理解的敘事,失去獵場的獵人,真的
就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網。
也許,我們可以進一步將獵人身體理解為已經融入了獵場土地氣息的身軀,這個氣息是活生
生地雜揉了長期以來吃下肚裏的各種野味,味道可能鮮美甘甜或血腥腐臭,但同樣都難以清除,
記憶也無法抺滅。只是這片傳統獵場早已屬於國家所有土地,今天已經是完全禁止狩獵的國家公
園。我問這位老獵人對這國家公園的感覺,他只淡淡地回應,「這有什麼辦法呢?我過去打獵是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