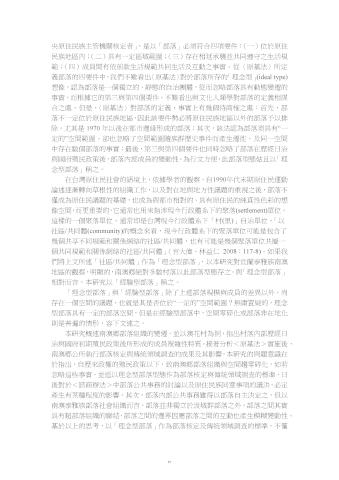Page 101 - 第六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101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是以「部落」必須符合四項要件:(一)位於原住
民族地區內;(二)具有一定區域範圍;(三)存在相延承襲並共同遵守之生活規
範;(四)成員間有依前款生活規範共同生活及互動之事實。從〈原基法〉所定
義部落的四要件中,我們不難看出〈原基法〉對於部落所存的「理念型」(ideal type)
想像,認為部落是一個獨立的、靜態的自治團體,從而忽略部落具有動態變遷的
事實。而根據它的第三與第四個要件,不難看出與文化人類學對部落的定義相謀
合之處。但是,〈 原基法〉對部落的定義,事實上有幾個待商榷之處:首先,部
落不一定位於原住民族地區,因此該要件勢必將原住民族地區以外的部落予以排
除,尤其是 1970 年以後在都市邊緣形成的部落;其次,該法認為部落須具有“一
定的”空間範圍,卻也忽略了空間範圍隨族群歷史事件而產生遷徙,及同一空間
中存在數個部落的事實;最後,第三與第四個要件也同時忽略了部落在歷經日治
與國府殖民政策後,部落內部成員的變動性。為行文方便,此部落型態姑且以「理
念型部落」稱之。
在台灣原住民社會的語境上,依據學者的觀察,自1990年代末期原住民運動
論述逐漸轉向草根性的組織工作,以及對在地與地方性議題的重視之後,部落不
僅成為原住民議題的基礎,也成為與都市相對的、具有原住民的純真性色彩的想
像空間,而更重要的,它通常也用來指涉現今行政體系下的聚落(settlement)單位。
這樣的一個聚落單位,通常即是台灣現今行政體系下「村(里)」自治單位,「以
社區/共同體(community)的概念來看,現今行政體系下的聚落單位可能是包含了
幾個共享不同規範和關係網絡的社區/共同體,也有可能是幾個聚落單位共屬一
個共同規範和關係網絡的社區/共同體」(官大偉、林益仁 2008:117-8)。如果我
們將上文所述「社區/共同體」作為「理念型部落」,以本研究對宜蘭泰雅族南澳
地區的觀察,明顯的,南澳鄉絕對多數村落以此部落型態存之。與「理念型部落」
相對而言,本研究以「經驗型部落」稱之。
「理念型部落」與「經驗型部落」除了上述部落規模與成員的差異以外,尚
存在一個空間的議題,也就是其是否位於“一定的”空間範圍?無庸置疑的,理念
型部落具有一定的部落空間,但是在經驗型部落中,空間零碎化或部落非在地化
則是普遍的情形,容下文述之。
本研究概述南澳鄉部落組織的變遷,並以澳花村為例,指出村落內部歷經日
治與國府初期殖民政策後所形成的成員複雜性特質。接著分析<原基法>實施後,
南澳鄉公所執行部落核定與傳統領域調查的成果及其影響。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在
於指出,自歷來政權的殖民政策以下,致南澳鄉部落組織與空間趨零碎化,如若
忽略這些事實,並逕以理念型部落型態作為部落核定與傳統領域調查的標準,日
後對於<諮商辦法>中部落公共事務的討論以及原住民族同意事項的議決,必定
產生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其次,部落內部公共事務雖得以部落自主決定之,但以
南澳泰雅族部落社會組織而言,部落並非獨立於流域群部落之外,部落之間其實
具有超部落組織的聯結,部落之間的邊界因應部落之間的互動也產生模糊變動性。
基於以上的思考,以「理念型部落」作為部落核定及傳統領域調查的標準,不僅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