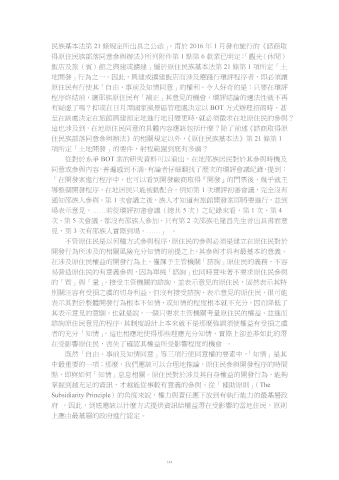Page 138 - 第六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138
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規定所出具之公函」。甫於 2016 年 1 月發布施行的《諮商取
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所列附件第 1 點第 6 款業已明定:「觀光(休閒)
飯店及旅(賓)館之興建或擴建」屬於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定「土
地開發」行為之一。因此,興建或擴建飯店而涉及應踐行環評程序者,即必須讓
原住民有行使其「自由、事前及知情同意」的權利。令人好奇的是:只要在環評
程序終結前,讓邵族原住民有「補正」其意見的機會,環評結論的適法性就不再
有疑慮了嗎?抑或在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決定以 BOT 方式辦理招商時,甚
至在該處決定在旅館興建預定地進行地目變更時,就必須徵求在地原住民的參與?
這也涉及到,在地原住民同意的具體內容應該包括什麼?除了前述《諮商取得原
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的相關規定以外,《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定「土地開發」的要件,射程範圍到底有多廣?
從對於系爭 BOT 案的研究資料可以看出,在地邵族居民對於其參與時機及
同意或參與內容,普遍感到不滿。有論者仔細翻找了歷次的環評會議紀錄,提到:
「在開發案進行程序中,也可以看到開發廠商取得『開發』的門票後,幾乎就主
導整個開發程序,在地居民只能被動配合。例如第 1 次環評初審會議,完全沒有
通知邵族人參與。第 1 次會議之後,族人才知道有旅館開發案即將要進行,並到
場表示意見。……若從環評初審會議(總共 5 次)之紀錄來看,第 1 次、第 4
次、第 5 次會議,都沒有邵族人參加,只有第 2 次邵族毛隆昌先生曾出具書面意
見,第 3 次有邵族人實際到場。……」 。
不管原住民是以何種方式參與程序,原住民的參與必須是建立在原住民對於
開發行為所涉及的相關風險充分知情的前提之上,其參與才具有最基本的意義。
在涉及原住民權益的開發行為上,僅課予主管機關「諮詢」原住民的義務,不容
易營造原住民的有意義參與,因為單純「諮詢」也同時意味著不要求原住民參與
的「質」與「量」。接受主管機關的諮詢,並表示意見的原住民,固然表示其特
別關注容有受損之虞的切身利益,但沒有接受諮詢、表示意見的原住民,很可能
表示其對於整體開發行為根本不知情,或知情的程度根本就不充分,因而降低了
其表示意見的意願。也就是說,一個只要求主管機關考量原住民的權益、並進而
諮詢原住民意見的程序,其制度設計上本來就不是那麼強調須使權益有受損之虞
者的充分「知情」,這也相應地使得那些理應充分知情,實際上卻並非如此的潛
在受影響原住民,喪失了確認其權益所受影響程度的機會 。
既然「自由、事前及知情同意」等三項行使同意權的要素中,「知情」是其
中最重要的一項;那麼,我們應該可以合理地推論,原住民參與開發程序的時間
點,即與如何「知情」息息相關。原住民對於涉及其自身權益的開發行為,能夠
掌握到越充足的資訊,才越能從事較有意義的參與。從「補助原則」(The
Subsidiarity Principle)的角度來說,權力與責任應下放到有執行能力的最基層政
府 ,因此,到底應該以什麼方式提供資訊給權益潛在受影響的當地住民,原則
上應由最基層的政府進行認定。
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