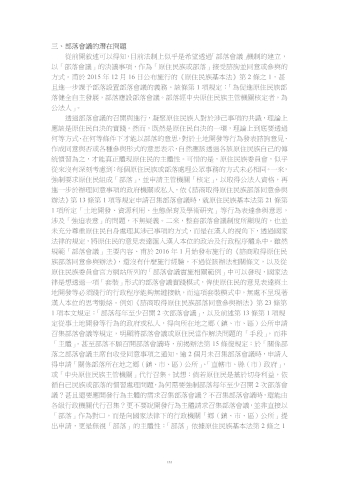Page 136 - 第六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136
三、部落會議的潛在問題
從前開敘述可以得知,目前法制上似乎是希望透過「部落會議」機制的建立,
以「部落會議」的決議事項,作為「原住民族或部落」接受諮詢並同意或參與的
方式。甫於 2015 年 12 月 16 日公布施行的《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 條之 1,甚
且進一步課予部落設置部落會議的義務。該條第 1 項規定:「為促進原住民族部
落健全自主發展,部落應設部落會議。部落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為
公法人」。
透過部落會議的召開與進行,凝聚原住民族人對於涉己事項的共識,理論上
應該是原住民自決的實踐。然而,既然是原住民自決的一環,理論上到底要透過
何等方式、在何等條件下才能以部落的意思,對於土地開發等行為發表諮詢意見、
作成同意與否或各種參與形式的意思表示,自然應該透過各該原住民族自己的傳
統慣習為之,才能真正體現原住民的主體性。可惜的是,原住民族委員會,似乎
從來沒有深刻考慮到:每個原住民族或部落處理公眾事務的方式未必相同。一來,
強制要求原住民組成「部落」,並申請主管機關「核定」,以取得公法人資格,再
進一步於辦理同意事項的政府機關或私人,依《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
辦法》第 13 條第 1 項等規定申請召集部落會議時,就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定「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等行為表達參與意思,
涉及「強迫表意」的問題,不無疑義。二來,整套部落會議制度所顯現的,也並
未充分尊重原住民自身處理其涉己事項的方式,而是在漢人的視角下,透過國家
法律的規定,將原住民的意見表達匯入漢人本位的政治及行政程序體系中。雖然
規範「部落會議」主要內容、甫於 2016 年 1 月始發布施行的《諮商取得原住民
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還沒有什麼施行經驗,不過從該辦法相關條文,以及從
原住民族委員會官方網站所列的「部落會議實施相關範例」中可以發現,國家法
律是想透過一項「套裝」形式的部落會議實踐模式,俾使原住民的意見表達與土
地開發等必須踐行的行政程序能夠無縫接軌,而這項套裝模式中,無處不呈現著
漢人本位的思考脈絡。例如《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第 23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部落每年至少召開 2 次部落會議」,以及前述第 13 條第 1 項規
定從事土地開發等行為的政府或私人,得向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申請
召集部落會議等規定,明顯將部落會議或原住民當作解決問題的「手段」,而非
「主體」。甚至部落不願召開部落會議時,前揭辦法第 15 條復規定:於「關係部
落之部落會議主席自收受同意事項之通知,逾 2 個月未召集部落會議時,申請人
得申請「關係部落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直轄市、縣(市)政府」,
或「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代行召集。試想:倘若原住民是基於切身利益,依
循自己民族或部落的慣習處理問題,為何需要強制部落每年至少召開 2 次部落會
議?甚且還要應開發行為主體的需求召集部落會議?不召集部落會議時,還能由
各級行政機關代行召集?更不要說開發行為主體請求召集部落會議,並非直接以
「部落」作為對口,而是向國家法律下的行政機關「鄉(鎮、市、區)公所」提
出申請,更是無視「部落」的主體性:「部落」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 條之 1
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