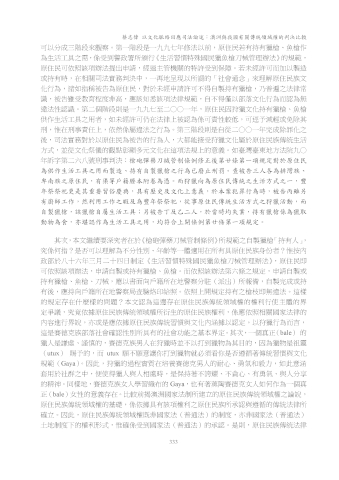Page 347 - 第二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347
蔡志偉 以文化脈絡回應司法論述:澳洲與我國有關傳統領域權的判決比較
可以分成三階段來觀察。第一階段是一九九七年修法以前,原住民若有持有獵槍、魚槍作
為生活工具之需,係受到警政署所頒行《生活習慣特殊國民獵魚槍刀械管理辦法》的規範,
原住民可依照該項辦法提出申請,經過主管機關的特許受到保障。若未經許可而加以製造
或持有時,在相關司法實務判決中,一再地呈現以所謂的「社會通念」來理解原住民族文
化行為,諸如指稱被告為原住民,對於未經申請許可不得自製持有獵槍,乃普遍之法律常
識,被告雖受教育程度非高,應該知悉該項法律規範,自不得僅以部落文化行為而認為無
違法性認識。第二個階段則是一九九七至二○○一年,原住民因狩獵文化持有獵槍、魚槍
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如未經許可仍在法律上被認為係可責性較低,可逕予減輕或免除其
刑,惟在刑事責任上,依然係屬違法之行為。第三階段則是自從二○○一年完成除罪化之
後,司法實務對於以原住民為被告的行為人,大都能接受狩獵文化屬於原住民族傳統生活
方式,並從文化祭儀的觀點彰顯多元文化在這項法規上的意義。如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九○
年訴字第二六八號刑事判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修正後第廿條第一項規定對於原住民
為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而製造、持有自製獵槍之行為已廢止刑罰。查被告三人各為排灣族、
卑南族之原住民,有渠等戶籍謄本附卷為憑。而狩獵向為原住民傳統之生活方式之一,豐
年祭祭祀更是其重要習俗慶典,具有歷史及文化上意義,於本案犯罪行為時,被告丙雖另
有廚師工作,然利用工作之暇及為豐年祭祭祀,從事原住民傳統生活方式之狩獵活動,而
自製獵槍,該獵槍自屬生活工具;另被告丁及乙二人,於當時均失業,持有獵槍係為獵取
動物為食,亦堪認作為生活工具之用,均符合上開條例第廿條第一項規定。
其次,本文繼續要深究者在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規範之自製獵槍「持有人」,
究係何指?是否可以理解為不分性別、年齡等一體適用在所有具原住民族身份者?惟按內
政部於八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制定《生活習慣特殊國民獵魚槍刀械管理辦法》,原住民即
可依照該項辦法,申請自製或持有獵槍、魚槍。而依照該辦法第六條之規定,申請自製或
持有獵槍、魚槍、刀械,應以書面向戶籍所在地警察分駐(派出)所報備,自製完成或持
有後,應持向戶籍所在地警察局查驗烙印給照。依照上開規定持有之槍枝即無違法。這樣
的規定存在什麼樣的問題?本文認為這邊存在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的權利行使主體的界
定爭議,究竟依據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所衍生的原住民族權利,係應依照相關國家法律的
內容進行界說,亦或是應依據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與文化內涵據以認定。以狩獵行為而言,
這是賽德克族部落社會確認性別所具有的社會功能之基本界定。其次,一個真正(bale) 的
獵人是謙虛、謹慎的,賽德克族男人在狩獵時並不以打到獵物為其目的,因為獵物是祖靈
(utux) 賜予的,而 utux 願不願意讓你打到獵物就必須看你是否遵循著傳統習慣與文化
規範(Gaya)。因此,狩獵的過程實質在培養賽德克男人的耐心、勇氣和毅力,如此意涵
套用於社群之中,便使得獵人與人相處時,是保持著不誇耀、不貪心、有勇氣、與人分享
的精神。同樣地,賽德克族女人學習織布的 Gaya,也有著薰陶賽德克女人如何作為一個真
正 ( bale)女性的意義存在。比較前揭澳洲國家法制所建立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之論說,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的基礎,係依據具有該項權利之原住民族所承認與遵循的傳統法律所
確立。因此,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既非國家法(普通法)的制度,亦非國家法(普通法)
土地制度下的權利形式,惟確係受到國家法(普通法)的承認。是則,原住民族傳統法律
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