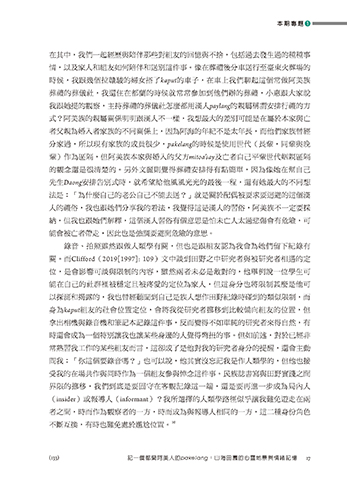Page 133 - 原住民族文獻第9輯
P. 133
本期專題 1
在其中,我們一起經歷與陪伴那些對組友的回憶與不捨,包括過去發生過的種種事
情,以及家人和組友如何陪伴和送別這件事。像在葬禮後分車送行至臺東火葬場的
時候,我跟幾個拉贛駿的婦女搭了kaput的車子,在車上我們聊起這個常做阿美族
葬禮的葬儀社,我還住在都蘭的時候就常常參加到他們辦的葬禮,小惠跟大家說
我跟她提的觀察,主持葬禮的葬儀社怎麼都用漢人paylang的親屬稱謂安排行禮的方
式?阿美族的親屬關係明明跟漢人不一樣,我想最大的差別可能是在屬於本家與亡
者父親為婚入者家族的不同關係上,因為阿海的年紀不是太年長,而他們家族曾經
分家過,所以現有家族的成員很少,pakelang的時候是使用世代(長輩,同輩與晚
輩)作為區隔,但阿美族本家與婚入的父方mitoa’say及亡者自己平輩世代姻親區隔
的觀念還是很清楚的。另外文麗則覺得葬禮安排得有點簡單,因為像她在幫自己
先生Daong安排告別式時,就希望給他風風光光的最後一程,還有她最大的不同想
法是:「為什麼自己的老公自己不能去送?」就是關於配偶被要求要迴避的這個漢
人的禮俗,我也跟她們分享我的看法,我覺得這是漢人的習俗,阿美族不一定要採
納,但我也跟她們解釋,這個漢人習俗有個意思是怕未亡人太過悲傷會有危險,可
能會被亡者帶走,因此也是強調要避開危險的意思。
錄音、拍照雖然跟做人類學有關,但也是跟組友認為我會為她們留下紀錄有
關。而Clifford(2019[1997]: 109)文中談到田野之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相遇的定
位,是會影響可談與限制的內容,雖然兩者未必是敵對的,他舉例說一位學生可
能在自己的社群裡被穩定且被疼愛的定位為家人,但這身分也將限制甚麼是他可
以探測和揭露的,我也曾經聽聞到自己是族人想作田野紀錄時碰到的類似限制,而
身為kaput組友的社會位置定位,會將我從研究者挪移到比較偏向組友的位置,但
拿出相機與錄音機和筆記本記錄這件事,反而變得不如單純的研究者來得自然,有
時還會成為一個特別讓我也讓某些身邊的人覺得彆扭的事。但如前述,對於已經非
常熟習我工作的某些組友而言,這卻成了是他對我的研究者身分的提醒,還會主動
問我:「你這個要錄音嗎?」也可以說,他其實沒忘記我是作人類學的,但他也接
受我的在場共作與同時作為一個組友參與悼念這件事。民族誌書寫與田野實踐之間
界限的挪移,我們到底是要固守在客觀記錄這一端,還是要再進一步成為局內人
(insider)或報導人(informant)?我所選擇的人類學路徑似乎讓我難免遊走在兩
者之間,時而作為觀察者的一方,時而成為與報導人相同的一方,這二種身份角色
不斷互換,有時也難免處於尷尬位置。 10
(133) 記一個都蘭阿美人的pakelang:山海田園的心靈地景與情緒記憶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