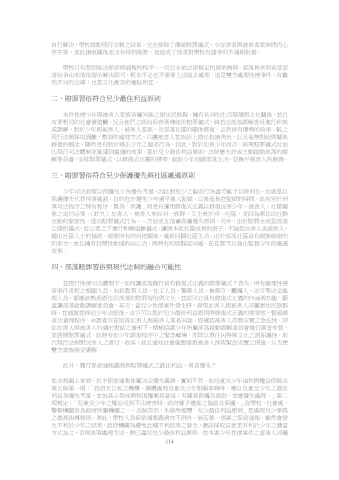Page 118 - 第四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118
自行解決,學校啟動現行法制之結果,完全排除了傳統賠罪儀式,令加害者與被害者家族間仍心
存芥蒂,彼此傷痕關係並沒有得到復原,這造成了部落對學校有諸多的不滿與指責。
學校只有想到依法保密與通報的程序,一切完全依法律規定快速地辦理。部落長老則希望部
落紛爭由部落依習俗解決即可,根本不必也不需要上法庭去處理。這是雙方處理性侵事件,有截
然不同的立場,也是文化衝突的癥結所在。
二、賠罪習俗符合兒少最佳利益原則
本件性侵少年與被害人家族皆屬同族之原住民族群,擁有共同的生活環境與文化關係,並且
有著相同的社會價值觀,況且他們之間尚保存著傳統的賠罪儀式,倘若由部落調解委員進行仲裁
或調解,對於少年與被害人、被害人家族、及部落社區的關係修復,必然具有優勢的效果。較之
現行法制採取隔離、割裂的處理方式,只讓被害人在訴訟上擔任指證角色,以及毫無對話與關係
修復的概念,顯然更有助於矯正少年之偏差行為。因此,對於加害少年而言,採用賠罪儀式反而
比現行司法體制更能達到處遇的效果。基於兒少最佳利益原則,法院應允許或主動啟動部落的調
解委員會,安排賠罪儀式,以修復式正義的精神,協助少年回歸部落生活,並撫平被害人的創傷。
三、賠罪習俗符合兒少保護優先與社區處遇原則
少年司法政策以保護兒少為優先考量,因此對兒少之偏差行為盡可能予以除刑化,也就是以
保護優先代替刑事處罰,目的在於避免少年過早進入監獄,日後延長在監獄的時間。此有別於刑
事司法程序之特有程序,既為「保護」則更有運用修復式正義以修復加害少年、被害人、社區關
係之迫切必要。(註九)加害人、被害人來自同一族群,又生長於同一社區,更因為原住民社群
互動的緊密性,透由賠罪儀式行為,一方面更加落實保護優先原則。另外,由於賠罪全或是部落
公開的儀式,在公眾之下進行和解道歉儀式,讓原本在社區成長的孩子,不論是加害人或被害人,
藉由社區人士的協助,復原所有的自他關係,重新回歸社區生活。由於部落社區具有親族綿密的
約束力,並且擁有封閉性地域的向心力,與特有的族群認同感,在在都可以強化監督少年的處遇
效果。
四、部落賠罪習俗與現代法制的融合可能性
在現行性侵司法體制下,如何讓部落踐行具有修復式正義的賠罪儀式?首先,所有處理性侵
害事件流程之相關人員,包括教育人員、社工人員、警察人員、檢察官、觀護人、法官等法定處
理人員,都應該熟悉原住民部落的賠罪習俗與文化,並認同它具有修復式正義的內涵與功能,願
意讓部落啟動調解委員會。其次,當兒少性侵案件發生時,發現加害人與被害人同屬原住民族群
時,在通報並移送少年法庭後,法官可以基於兒少最佳利益原則與修復式正義的需要性,暫緩調
查及審理程序,命調查官在取得加害人與被害人家長同意,經確認被害人亦無安置之急迫性,評
估加害人與被害人均適於對話之情形下,積極協調少年所屬部落啟動調解委員會進行調查仲裁,
並展開賠罪儀式。此時有如少年調查程序中之緊急輔導,亦即以原住民特殊文化之需保護性,取
代現行法制對加害人之責付、收容,並且通知社會處暫緩對被害人採取緊急安置之措施,以方便
雙方家族接受調解。
此外,履行保密通報義務與賠罪儀式之最佳利益,何者優先?
從法規範上來看,似乎保密通報係屬法定優先義務,實則不然。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五條第一項:「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處理兒童及少年相關事務時,應以兒童及少年之最佳
利益為優先考量,並依其心智成熟程度權衡其意見;有關其保護及救助,並應優先處理。」第二
項規定:「兒童及少年之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時,政府應予適當之協助及保護。」從學校、社會處、
警察機關皆為政府所屬機關之一,法院亦然。本條所揭櫫「兒少最佳利益原則」是處理兒少事務
之最高指導原則。準此,學校人員保密通報義務亦不例外,倘若某一個案之保密通報,顯然會發
生不利於少年之結果,政府機關為避免此種不利結果之發生,應該採取其他更有利於少年之適當
方式為之,否則該項處理方法,便已違反兒少最佳利益原則。在本案少年性侵案件之當事人同屬
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