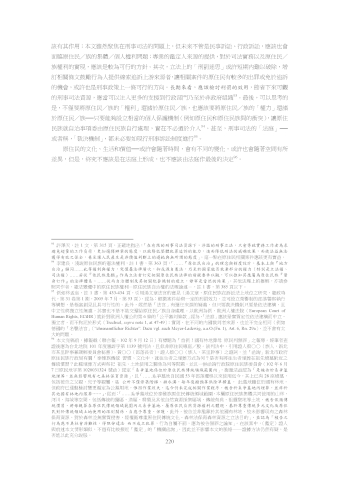Page 224 - 第四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224
該有其作用;本文雖然聚焦在刑事司法的問題上,但未來不管是民事訴訟、行政訴訟,應該也會
面臨原住民/族的集體/個人權利問題;專業的鑑定人來源的提供,對於司法實務以及原住民/
族權利的實現,應該是較為可行的方針。其次,立法上的「刑罰迷思」或許短期內難以破除,增
訂相關條文鼓勵行為人提供線索追訴上游來源者,讓相關案件的原住民有較多的出罪或免於追訴
的機會,或許也是刑事政策上一條可行的方向。長期來看,應該檢討刑罰的效用,節省下來可觀
93
的刑事司法資源,應當可以注入更多的支援到行政部門乃至於非政府組織 。最後,可以思考的
是,不僅要將原住民/族的「權利」還諸於原住民/族,也應該要將原住民/族的「權力」還諸
於原住民/族──只要能夠設立相當的個人保護機制(例如原住民和原住民族間的衝突),讓原住
94
民族就自治事項委由原住民族自行處理,實在不必過於介入 。甚至,刑事司法的「法庭」──
95
或者稱,「裁決機制」,都未必要如現行刑事訴訟制度進行 。
原住民的文化、生活和價值──或許會隨著時間,會有不同的變化,或許也會隨著空間有所
96
差異,但是,終究不應該是在法庭上形成,也不應該由法庭作最後的決定 。
93
許澤天,註 1 文,第 315 頁,正確地指出:「在有限的刑事司法資源下,浮濫的刑事立法,只會導致實務工作者為求
避免超量的工作負荷,更加選擇辦案的態度,以致降低整體犯罪追訴的能力,進而降低刑法的威嚇效果,而使法益無法
獲得有效之保全,甚至讓人民產生是非價值判斷上的遲鈍與無所謂的態度」。這一點在原住民相關案件應該更有實益。
94
李建良,淺說原住民族的憲法權利,註 1 書,第 363 頁:「……『原住民自治』的理念與制度設計,基本上與『地方
自治』類同……此等權利與權力,究僅屬法律層次,抑或源自憲法,乃至於國家能否放棄部分的權力(特別是立法權、
司法權)……若從『依民族意願』作為立法者訂定相關原住民族法律的前提要件以觀,可以推知其應屬為原住民族『量
身訂作』的法律體系。……從而自治體制及其相關配套機制的建立,毋寧是當然的結果」。 其他法理上的推解,亦請參
照同作者,憲法變遷中的原住民族權利-原住民族自治權的法理論述-,註 1 書,第 385 頁以下。
95
例如林孟皇,註 1 書,第 433-434 頁,引用湯文章法官的意見(湯文章,原住民族在訴訟法上地位之研究,憲政時
代,第 31 卷第 1 期,2005 年 7 月,第 53 頁),認為:輕微案件給與一定的刑罰效力、並可設立榮譽制的部落警察執行
等構想,是極富創見且具可行性的。此外,縱然是「法官」有選任來源的疑義,但只要裁決機制只要是依法建構,且
中立性與獨立性無虞,其實也不是不能交還給原住民/族自身處理。以歐洲為例,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CtHR)就針對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的「公平審判條款」認為,「法庭」應該是實質定性依法建構而中立、
獨立者,而不拘泥於形式(Trechsel, supra note 1, at 47-49);實則,在不同的內國裁判者來源,也並不完全相同(例如
德國的「名譽法官」(”ehrenamtlicher Richter”. Dazu vgl. auch Meyer-Ladewig, a.a.O.(Fn. 1), Art. 6, Rn. 29a),並不會有太
大的問題。
96 本文完稿前,據報載(聯合報,102 年 9 月 12 日)有標題為「首例!國有林地葬母 原民判無罪」之報導。經筆者查
證後應為台北地院 101 年度審訴字第 1139 號判決,且似非原住民專庭/股。該判決中,引用證人蔡○○(族人,新北
市某里幹事兼調解委員會秘書)、黃○○(部落長者),證人蔡○○(族人,某里幹事)之證詞,並「函詢」新北市政府
原住民族行政局有關「泰雅族傳統 習慣、文化中,就往生者之埋葬方式為何?是否有將往生者埋葬在祖先墳墓附近之
傳統慣習?此種埋葬方式與祭祀 祖先、土地使用之關係為何等問題。並且一併函詢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2 年 6 月
7 日原民地字第 1020031324 號函)認定「系爭墓地係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範圍內」,衡量法益認為「是被告於系爭墓
地埋葬,並無影響現有之森林保育資源」,且「……系爭墓地自民國 53 年部落遷移以來使用迄今,其上已有 28 座墳墓,
包括被告之父親、兒子等親屬,區 公所不僅修築階梯、排水溝,每年復撥預算供除草掃墓, 此墓地雖位於國有林地,
但政府已通盤檢討變更編定為公墓用地,惟因作業疏失,迄今仍未完成相關作業程序,被告於系爭墓地內埋葬,並非於
其他國有林地內濫葬……」,從而:「……系爭墓地位於泰雅族原住民傳統領域範圍,本屬原住民族集體共同使用的山林、
河川、海域等空間,包括傳統的獵區、漁區、耕墾及其他自然資源採集區域、傳統祭典、祖靈聖地等土地,被告依循傳
統慣習,將母親葬在原住民傳統領域範圍內之系爭墓地,屬原住民自然資源權利之體現,基於尊重傳統多元文化及原住
民對於傳統領域土地使用的深刻關係,自應予尊重、保護。此外,被告並非濫葬於其他國有林地,故未影響現有之森林
保育資源,對於森林並無實質侵害,經權衡尊重原住民傳統文化、森林法保育森林資源之立法目的」,並認為「被告之
行為應不具社會非難性,得阻卻違法 而不成立犯罪,行為自屬不罰,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在該案中,(鑑定)證人
與前述本文情形類似,不過有比較接近「鑑定」的「機關函詢」。因此並不影響本文的脈絡──證據方法仍然有疑,是
否能以此充分說服。
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