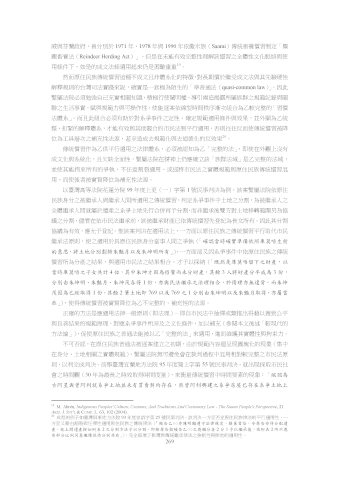Page 273 - 第四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273
威與芬蘭政府,曾分別於 1971 年、1978 年與 1990 年依撒米族(Saami)傳統畜養慣習制定「麋
鹿畜養法(Reindeer Herding Act)」,但是在未能有效完整性理解該慣習之全體性文化脈絡與使
19
用條件下,如是的成文法條適用起來仍是困難重重 。
然而原住民族傳統慣習這種不成文且非體系化的特徵,對長期慣於繼受成文法與其先驗硬性
解釋規則的台灣司法實踐來說,確實是一套極為陌生的「準普通法(quasi-common law)」。因此
繫屬法院必須勉強自己充實相關知識,積極行使闡明權,導引兩造揭露所屬族群之規範紀錄與關
聯之生活事實,賦與規範力與可操作性,使能逐案依線型時間秩序漸次組合為乙較完整的「習慣
法體系」。而且此組合必須有助於對系爭事件之定性、確定規範適用條件與效果,並外顯為乙統
整、扣緊的解釋體系,才能有效與其他競合的市民法制平行適用,否則往往反而使傳統慣習被降
20
位為工具層次之補充性法源,甚至造成去規範化與去道德化的反效果 。
傳統慣習作為乙供平行適用之法律體系,必須被認知為乙「完整的法」,即使在外觀上沒有
成文化與系統化,且欠缺全面性,繫屬法院在精神上仍應確立該「族群法域」是乙完整的法域,
並使其能拘束所有的爭執,不任意割裂適用,或逕將市民法之實體規範與原住民族傳統慣習混
用,而使後者被實質降位為補充性法源。
以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99 年度上更(一)字第 1 號民事判決為例,該案繫屬法院依原住
民族身分之被繼承人與繼承人間所適用之傳統慣習,判定系爭事件中土地之分割,為被繼承人之
全體繼承人間就屬於遺產之系爭土地先行合併再予分割,而非繼承後雙方對土地移轉範圍另為協
議之分割,儘管在依市民法繼承前,該被繼承財產已依傳統慣習先登記為長女所有。因此其分割
協議為有效,應允予登記。惟該案判決在適用法上,一方面以原住民族之傳統慣習平行取代市民
繼承法原則,使之適用於具原住民族身分當事人間之爭執(「確認當時確實準備依照庫莫唔生前
的意思,將土地分別劃歸朱豔月以及朱坤明所有」),一方面卻又因系爭事件中依原住民族之傳統
慣習所為分產之結果,與適用市民法之結果相合,才予以採納(「既然是庫莫唔留下之財產,以
當時庫莫唔之子女共計 4 位,其中朱坤才因為招贅而未分財產,其餘 3 人將財產分平成為 3 份,
分別由朱坤明、朱豔月、朱坤茂各得 1 份,亦與民法繼承之法理相合,於情理亦無違背。而朱坤
茂因為已經取得 1 份,其餘 2 筆土地即 769 以及 769 之 1 分別由朱坤明以及朱豔月取得,亦屬當
然」),使得傳統慣習被實質降位為乙不完整的、補充性的法源。
正確的方法是應適用法律一般原則(即法理)-即自市民法中抽繹或類推出得藉以獲致公平
與良善結果的規範原理,對應系爭事件所涉及之文化條件,加以補充(參閱本文後述「較現代的
方法論」),促使原住民族之普通法能被以乙「完整的法」來適用,進而維護其實體性與拘束力。
不可否認,在原住民族普通法被逐案建立之初期,由於規範內容還呈現團塊化的現象(集中
在身分、土地相關之實體規範),繫屬法院無可避免會在裁判過程中混用相對較完整之市民法原
則,以利完成判決。前舉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95 年度簡上字第 55 號民事判決,就出現採取市民社
會之時間觀(30 年為最長之時效取得時間度量),來衡量傳統慣習中時間要素的現象:「縱認為
古阿星與曾阿利就系爭土地並未有買賣契約存在,然曾阿利興建之系爭房屋已存在系爭土地上
19
M. Ahrén, Indigenous Peoples' Culture, Customs, And Traditions And Customary Law - The Saami People's Perspective, 21
ARIZ. J. INT'L & COMP. L. 63, 102 (2004).
20
典型的例子如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93 年度家訴字第 25 號民事判決。該判決一方面否定原住民族律法的平行適用性,一
方面又藉由割裂與任擇性適用原住民族之傳統律法(「被告乙○○亦陳明願遵守法律規定,摒棄習俗,令原告亦得分配遺
產,就上開遺產按如附表 2 之分割方法予以分割,即按原告與被告乙○○之應繼分各 2 分 1 予以繼承後,依附表 2 所示應
有部分比例同意繼續保持分別共有」), 完全破壞了排灣族傳統繼承律法之強制性與排他的適用性。
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