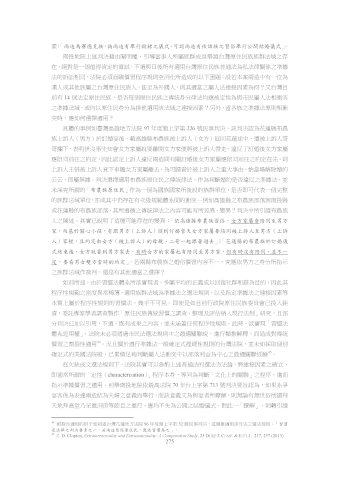Page 279 - 第四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279
素:「 兩造為賽德克族,倘兩造有舉行殺豬之儀式,可認兩造有依該族之習俗舉行公開結婚儀式」。
南投地院上述判決藉由闡明權,引導當事人所屬族群成員舉證台灣原住民族族群法域之存
在 , 絕對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嘗試。不過與日後所有適用台灣原住民族普通法為私法律關係之準據
法的訴訟相同,法院必須面臨慣習程序規則空洞化所造成的以下困題:設若本案兩造中有一位為
漢人或其他族屬之台灣原住民族人,甚至為外國人,則其適當之屬人法連接因素為何?又台灣目
前有 14 個法定原住民族,是否每個原住民族之傳統身分律法均應被定性為與市民屬人法相衝突
之準據法域,或均以原住民身分為排他適用該法域之連接因素?另外,當各族之準據法原則相衝
突時,應如何選擇適用?
具體的事例如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7 年度簡上字第 226 號民事判決。該判決認為花蓮縣布農
族上訴人(男方)於訂婚宴後,載高雄縣布農族被上訴人(女方)返回花蓮途中,遭被上訴人哥
哥攔下,表明伊沒事先知會女方家屬說要離開女方家便將被上訴人帶走,違反了訂婚後女方家屬
應陪同前往之約定,因此認定上訴人違反兩造間有關訂婚後女方家屬應陪同前往之約定在先,則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竟下車隨女方家屬離去,為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重大事由,始當場解除婚約
云云,即屬無據。判決選擇適用布農族原住民之傳統律法,作為判斷婚約是否違反之準據法,並
未深究所謂的「布農族原住民」作為一個為國族國家所後設的族群單位,是否即可代表一個完整
的族群法域單位,亦或其中仍存在有次級規範體系間的衝突—例如高雄縣之布農族部落與南投縣
或花蓮縣的布農族部落,其所遵循之傳統律法之內容可能有所差異、變異?判決中所引證布農族
人之陳述,其實已說明了這種可能存在的變異:「依高雄縣布農族習俗,女方家屬會陪同至男方
家,而基於關心小孩,有跟男方(上訴人)談到訂婚當天女方家屬要陪同被上訴人至男方(上訴
人)家裡,且約定由女方(被上訴人)的母親、二哥一起跟著過去」;「花蓮縣的布農族於訂婚儀
式結束後,女方就要到男方家去,有時女方的家屬也有陪同至男方家,但有時沒有陪同,並不一
定,要看男女雙方當時的約定」。若兩縣布農族之婚俗慣習內容不一,究應依男方之身分所指示
之族群法域作裁判,還是有其他適當之選擇?
如前所述,由於習慣法體系所欲實現者,多屬平均的正義或以回復社群和諧為目的,因此其
程序性規範之密度異常稀薄,適用族群法域為準據法之選法規則, 以 及指定準據法之連接因素等
本質上屬於程序性規則的習慣法,幾乎不可見。即使是如目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已投入鉅
資,委託專家學者調查製作「原住民族傳統習慣之調查、整理及評估納入現行法制」研究,且部
分判決已加以引用,不過,既有成果之內容,並未涵蓋任何程序性規則。此時,欲實現「習慣法
體系近用權」,法院未必須透過市民法選法規則中之最適關聯說,進行類推解釋,而造成對傳統
44
慣習之割裂性適用 。況且慣於遵行準據法一般確定式裡硬性規則的台灣法院,並未如採取個別
45
確定式的美國法院般,已累積足夠判斷屬人法衝突中以部落利益為中心之最適關聯經驗 。
在欠缺成文選法規則下,法院其實可以參酌上述普通法的選法方法論,將連接因素之確立,
即通常所謂的「定性(characterization)」程序本身,等同為判斷「文化上的關聯」之程序,進而
指示準據慣習之適用。前舉南投地院依最高法院 70 年台上字第 713 號判決要旨認為,如果系爭
宴客係為表達兩造結為夫婦之意義而舉行,而該意義又為與宴者所瞭解,則無論有無世俗所謂拜
天地拜高堂乃至進洞房等節目之進行,應均不失為公開之結婚儀式。對此一「瞭解」,則轉引證
44 割裂性適用的例子如前述台灣花蓮地方法院 96 年度簡上字第 32 號民事判決,逕類推適用涉外法之選法規則:「習慣
是法律之判決要素之一,若兩造皆係原住民,應依習慣為之」。
45
Z. D. Clopton,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Extranationality: A Comparative Study, 23 DUKE J. COMP. & INT'L L. 217, 257 (2013)
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