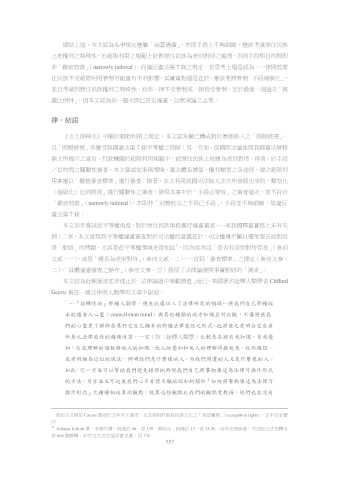Page 361 - 第四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361
總結上述,本文認為系爭規定應屬「涵蓋過廣」,亦即手段上不夠細緻,應該考量原住民族
土地權利之特殊性,於超限利用之規範上針對原住民族為差別對待之處理,否則手段與目的間即
非「嚴密剪裁」(narrowly tailored),而違反憲法第 7 條之規定。若思考上還是認為,一律開放原
住民族不受超限利用管制可能會有不利影響,其實重點還是在於,應該要將管制「手段細緻化」,
並且考量到原住民族權利之特殊性,而非一律不受管制或一律皆受管制。至於最後一個層次「狹
義比例性」,因本文認為前一層次即已宣告違憲,自無深論之必要。
肆、結語
《水土保持法》中關於超限利用之規定,本文認為實已構成對於原鄉族人之「間接歧視」,
且「間接歧視」亦應受我國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之保障;另一方面,從國際法論述與我國憲法增修
條文所揭示之意旨,行政機關於超限利用規範中,就原住民族土地應為差別對待。再者,於手段
/目的間之關聯性審查,本文嘗試從事務領域、憲法體系價值、權利類型之各途徑,證立超限利
用案應以「嚴格審查標準」進行審查;接著,本文利用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所發展出來的「類型化
(層級化)比例原則」進行關聯性之審查,發現本案中於「手段必要性」之審查層次,並不符合
「嚴密剪裁」(narrowly tailored),亦即非「別無他法之不得已手段」,手段並不夠細緻,故違反
憲法第 7 條。
本文初步嘗試從平等權角度,對於原住民族事務進行違憲審查,一來我國釋憲實務上未有先
例;二來,本文發現到平等權違憲審查對於司法權的意義在於:司法權幾乎難以避免要去面對背
74
景「脈絡」的問題,尤其是在平等權領域更是如此 ,因為從判定「是否有差別對待存在」(參前
文貳、一),或是「應否為差別對待」(參前文貳、二),一直到「審查標準」之擇定(參前文参、
二)、「具體違憲審查之操作」(參前文参、三)展現了法律論證與事實脈絡的「匯流」。
本文認為此種匯流並非僅止於「法律論證中乘載價值」而已,美國著名詮釋人類學者 Clifford
Geertz 曾在一篇法律與人類學的文章中說道:
「…『詮釋性的』那種人類學-便在此處切入了法律研究的領域…將我們自己那種版
本的議會人心靈(council-man mind)與其他種類的地方知識並列以觀,不僅將使我
們的心靈更了解那些異於它自己擁有的那種法律感性之形式,也將使之更明白它自身
所具之法律感性的精確性質。…它(按:詮釋人類學)比較是在將自我知識、自我覺
知、自我理解的過程與他人的知識、他人的覺知和他人的理解焊接起來,從而確認-
或者用極為近似的說法-辨明我們是什麼樣的人,而我們周遭的人又是什麼樣的人。
如此,它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避免錯謬地再現我們自己將事物陳述為法律可操作形式
的方法,另方面又可迫使我們心不甘情不願地認知到關於『如何將事物陳述為法律可
操作形式』之種種相歧異的觀點,就算這些觀點比我們的觀點更教條,他們也並沒有
然而本文對於 Carens 教授於文中所主張者,尤其是對於原住民族文化之「承認權利」( recognition rights), 並不完全贊
同。
74
Juliame Kokott 著,李惠宗譯,前揭註 48,頁 139。黃昭元,前揭註 13,頁 35-36。另外也請參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第 666 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7-8。
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