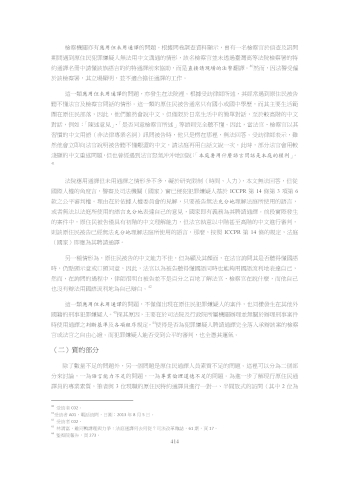Page 418 - 第四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418
檢察機關亦有應用但未用通譯的問題。根據問卷調查資料顯示,曾有一名檢察官於偵查及訊問
期間遇到原住民犯罪嫌疑人無法用中文溝通的情形,該名檢察官並未透過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的特
40
約通譯名冊中請懂該族語言的約特通譯前來協助,而是直接請現場的法警翻譯。 然而,因法警受僱
於該檢察署,其立場顯明,並不適合擔任通譯的工作。
這一類應用但未用通譯的問題,亦發生在法院裡。根據受訪律師所述,其經常遇到原住民被告
聽不懂法官及檢察官問話的情形。這一類的原住民被告通常只有國小或國中學歷,而其主要生活範
圍在原住民部落,因此,他們雖然會說中文,但僅限於日常生活中的簡單對話,至於較高階的中文
對話,例如:「陳述意見」、「是否同意檢察官所述」等語則完全聽不懂。因此,當法官、檢察官以其
習慣的中文用語(非法律專業名詞)訊問被告時,他只是楞在那裡,無法回答。受訪律師表示,雖
然他會立即向法官說明被告聽不懂艱澀的中文,請法庭再用白話文說一次,此時,部分法官會用較
淺顯的中文重述問題,但也曾經遇到法官怒氣沖沖地回說:「本庭要用什麼語言問話是本庭的權利」。
41
法院應用通譯但未用通譯之情形多不多,礙於研究限制(時間、人力),本文無法回答,但從
國際人權的角度言,警察及司法機關(國家)實已侵犯犯罪嫌疑人基於 ICCPR 第 14 條第 3 項第 6
款之公平審判權。理由在於依據人權委員會的見解,只要被告無法充分地理解法庭所使用的語言,
或者無法以法庭所使用的語言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國家即有義務為其聘請通譯。前段實際發生
的案件中,原住民被告僅具有初階的中文理解能力,但法官執意以中階甚至高階的中文進行審判,
則該原住民被告已經無法充分地理解法庭所使用的語言,那麼,按照 ICCPR 第 14 條的規定,法庭
(國家)即應為其聘請通譯。
另一種情形為,原住民被告的中文能力不佳,但為顧及其顏面,在法官詢問其是否聽得懂國語
時,仍點頭示意或口頭同意,因此,法官以為被告聽得懂國語同時也能夠用國語流利地表達自己,
然而,在詢問的過程中,律師很明白被告並不是百分之百地了解法官、檢察官在說什麼,而他自己
42
也沒有辦法用國語流利地為自己辯白。
這一類應用但未用通譯的問題,不僅僅出現在原住民犯罪嫌疑人的案件,也同樣發生在其他外
43
國籍的刑事犯罪嫌疑人。 探其原因,主要在於司法院及行政院所屬機關辦理並無關於辦理刑事案件
44
時使用通譯之判斷基準及各項程序規定, 使得是否為犯罪嫌疑人聘請通譯完全落入承辦該案的檢察
官或法官之自由心證。而犯罪嫌疑人能否受到公平的審判,也全憑其運氣。
(二)質的部分
除了數量不足的問題外,另一個問題是原住民通譯人員素質不足的問題。這裡可以分為二個部
分來討論,一為語言能力不足的問題,一為專業倫理道德不足的問題。為進一步了解現行原住民通
譯員的專業素質,筆者與 3 位現職的原住民特約通譯員進行一對一、半開放式的訪問(其中 2 位為
40
受訪者 C02。
41
受訪者 A01,電話訪問,日期:2013 年 8 月 5 日。
42
受訪者 C02。
43
林渭富,雞同鴨講理與力爭:法庭通譯何去何從?司法改革雜誌,61 期,頁 17。
44
監察院報告,頁 273。
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