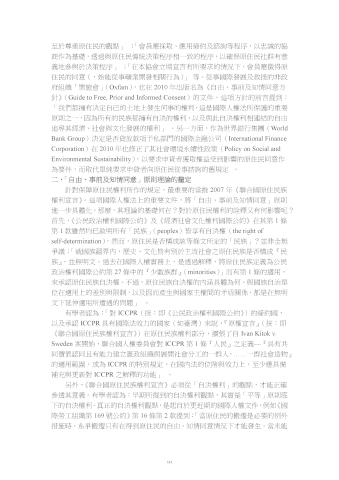Page 126 - 第六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126
至於尊重原住民的觀點」 ;「會員應採取、應用締約及諮詢等程序,以忠誠的協
商作為基礎,透過與原住民傳統決策程序相一致的程序,以確保原住民社群有意
義地參與於決策程序」 ;「在本協會立場宣言有所要求的情況下,會員應徵得原
住民的同意(,始能從事礦業開發相關行為)」 等。從事國際發展及救援的非政
府組織「樂施會」(Oxfam),也在 2010 年出版名為《自由、事前及知情同意方
針》(Guide to 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的文件。這項方針的前言提到:
「我們都擁有決定自己的土地上發生何事的權利,這是國際人權法所保護的重要
原則之一,因為所有的民族都擁有自決的權利,以及與此自決權利相連結的自由
追尋其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的權利」 。另一方面,作為世界銀行集團(World
Bank Group)決定是否貸放款項予私部門的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在 2010 年也修正了其社會環境永續性政策(Policy on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以要求申貸者獲取權益受到影響的原住民同意作
為要件,而取代單純要求申貸者向原住民從事諮詢的舊規定 。
二、「自由、事前及知情同意」原則理論的釐定
針對保障原住民權利所作的規定,最重要的當推 2007 年《聯合國原住民族
權利宣言》。這項國際人權法上的重要文件,將「自由、事前及知情同意」原則
進一步具體化。那麼,其理論的基礎何在?對於原住民權利的詮釋又有何影響呢?
首先,《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其第 1 條
第 1 款雖然均已敘明所有「民族」(peoples)皆享有自決權(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然而,原住民是否構成該等條文所定的「民族」?並非全無
爭議:「就國族疆界內,歷史、文化皆有別於主流社會之原住民族是否構成『民
族』,並無明文。過去在國際人權實務上,是透過解釋,將原住民族定義為公民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7 條中的『少數族群』(minorities)」而有第 1 條的適用,
來承認原住民族自決權。不過,原住民族自決權的內涵具體為何、與國族自治單
位在適用上的差別與限制,以及因而產生與國家主權間的矛盾關係,都是在無明
文下延伸適用所遭遇的問題」 。
有學者認為:「對 ICCPR(按:即《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締約國,
以及承認 ICCPR 具有國際法效力的國家(如臺灣)來說,『原權宣言』(按:即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在原住民族權利部分,擴張了自 Ivan Kitok v.
Sweden 案開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 ICCPR 第 1 條『人民』之定義—『具有共
同價值認同且有能力建立憲政組織與展開社會分工的一群人,……一群社會造物』
的適用範圍,或為 ICCPR 的特別規定,在國內法的位階與效力上,至少應具備
補充與更新對 ICCPR 之解釋的功能」 。
另外,《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必須從「自決權利」的觀點,才能正確
參透其意義。有學者認為:早期所提到的自決權利觀點,其實是「平等」原則底
下的自決權利。真正的自決權利觀點,是起自於更近期的國際人權文件,例如《國
際勞工組織第 169 號公約》第 16 條第 2 款提到:「當原住民的搬遷是必要的例外
措施時,系爭搬遷只有在得到原住民的自由、知情同意情況下才能發生。當未能
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