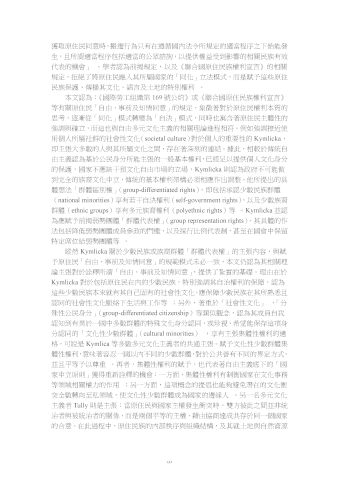Page 127 - 第六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127
獲取原住民同意時,搬遷行為只有在遵循國內法令所規定的適當程序之下始能發
生,且所謂適當程序包括適當的公眾諮詢,以提供權益受到影響的相關民族有效
代表的機會」 。學者認為前揭規定,以及《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相關
規定,拒絕了將原住民融入其所屬國家的「同化」立法模式,而是賦予這些原住
民族保護、傳播其文化、語言及土地的特別權利 。
本文認為:《國際勞工組織第 169 號公約》或《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等有關原住民「自由、事前及知情同意」的規定,象徵著對於原住民權利本質的
思考,逐漸從「同化」模式轉變為「自決」模式,同時也寓含著原住民主體性的
強調與確立,而這也與自由多元文化主義的相關理論進程相符。例如強調接近使
用個人所屬社群的社會性文化(societal culture)對於個人的重要性的 Kymlicka,
即主張大多數的人與其所屬文化之間,存在著深刻的連結。據此,相較於傳統自
由主義認為基於公民身分所能主張的一般基本權利,已經足以提供個人文化身分
的保護,國家不應該干預文化自由市場的立場,Kymlicka 則認為政府不可能做
到完全的族裔文化中立,傳統的基本權利架構必須相應作出調整。他所提出的具
體想法「群體區別權」(group-differentiated rights),即包括承認少數民族群體
(national minorities)享有若干自決權利(self-government rights),以及少數族裔
群體(ethnic groups)享有多元族裔權利(polyethnic rights)等 。Kymlicka 並認
為應賦予前揭弱勢團體「群體代表權」(group representation rights),其具體的作
法包括降低弱勢團體成員參政的門檻,以及採行比例代表制,甚至在國會中保留
特定席位給弱勢團體等 。
縱然 Kymlicka 關於少數民族或族裔群體「群體代表權」的主張內容,與賦
予原住民「自由、事前及知情同意」的規範模式未必一致,本文仍認為其相關理
論主張對於詮釋所謂「自由、事前及知情同意」,提供了紮實的基礎。理由在於
Kymlicka 對於包括原住民在內的少數民族,特別強調其自治權利的保障,認為
這些少數民族本來就有其自己固有的社會性文化,應保障少數民族在其所熟悉且
認同的社會性文化脈絡下生活與工作等 ;另外,著重於「社會性文化」 、「分
殊性公民身分」(group-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等類似觀念,認為其成員自我
認知到有異於一國中多數群體的特殊文化身分認同,或珍視、希望能保存這項身
分認同的「文化性少數群體」(cultural minorities) ,享有主張集體性權利的適
格,可說是 Kymlica 等多數多元文化主義者的共通主張。賦予文化性少數群體集
體性權利,意味著容忍一國以內不同的少數群體,對於公共善有不同的界定方式,
並且平等予以尊重 。再者,集體性權利的賦予,也代表著自由主義底下的「國
家中立原則」獲得重新詮釋的機會:一方面,集體性權利有制衡國家在文化事務
等領域相關權力的作用 ;另一方面,這項概念的提倡也能夠避免潛在的文化衝
突全數轉向至私領域,使文化性少數群體成為國家的邊緣人 。另一名多元文化
主義者 Tully 則是主張:當原住民與國家主權發生衝突時,雙方彼此之間並非統
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而是兩個平等的主權,藉由協商達成共存於同一個國家
的合意。在此過程中,原住民族的內部秩序與組織結構,及其就土地與自然資源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