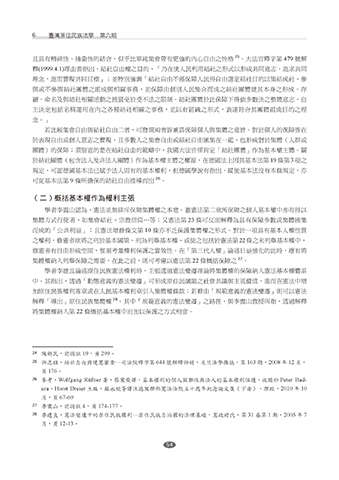Page 64 - 臺灣原住民族法學期刊第一卷第六期
P. 64
6 臺灣原住民族法學 第六期
25
且具有精神性、抽象性的結合,似乎比單純集會帶有更強的內心自由之性格 。大法官釋字第 479 號解
釋(1999.4.1)理由書指出,結社自由權之目的,「乃在使人民利用結社之形式以形成共同意志,追求共同
理念,進而實現共同目標」;並特別強調「結社自由不僅保障人民得自由選定結社目的以集結成社、參
與或不參與結社團體之組成與相關事務,並保障由個別人民集合而成之結社團體就其本身之形成、存
續、命名及與結社相關活動之推展免於受不法之限制。結社團體於此保障下得依多數決之整體意志,自
主決定包括名稱選用在內之各種結社相關之事務,並以有組織之形式,表達符合其團體組成目的之理
念。」
若比較集會自由與結社自由二者,可發現兩者皆兼具保障個人與集體之意旨。對於個人的保障皆在
於表現自由或個人意志之實現,且多數人之集會自由或結社自由匯集在一起,也形成對於集體(人群或
團體)的保障;須留意的是在結社自由的範疇中,我國大法官係肯定「結社團體」作為基本權主體。關
於結社團體(包含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作為基本權主體之權源,在德國法上因其基本法第 19 條第 3 項之
規定,可認德國基本法已賦予法人固有的基本權利,但德國學說有指出,縱使基本法沒有本條規定,亦
26
可從基本法第 9 條所擔保的結社自由推導而出 。
(二)概括基本權作為權利主張
學者李震山認為,憲法並無排斥保障集體權之本意。蓋憲法第二章所保障之個人基本權中亦有得以
集體方式行使者,如集會結社、宗教信仰…等;又憲法第 23 條可反面解釋為具有保障多數或集體匯集
而成的「公共利益」;且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亦不乏保護集體權之形式。對於一項具有基本人權性質
之權利,修憲者欲將之列於基本國策、列為列舉基本權、或使之包括於憲法第22條之未列舉基本權中,
修憲者有自由形成空間,惟須考量權利保護之實效性。在「第三代人權」論述日益強化的此時,應有將
27
集體權納入列舉保障之需要,在此之前,則可考慮以憲法第 22 條概括保障之 。
學者李建良論述原住民族憲法權利時,主張透過憲法變遷理論將集體權的保障納入憲法基本權體系
中。其指出,透過「動態意義的憲法變遷」可形成原住民議題之社會共識與主流價值,進而在憲法中增
加原住民族權利專章或在人民基本權利章引入集體權條款;若藉由「規範意義的憲法變遷」則可以憲法
28
解釋「導出」原住民族集體權 。其中「規範意義的憲法變遷」之路徑,與李震山教授所指,透過解釋
將集體權納入第 22 條概括基本權中而加以保護之方式相當。
24 陳新民,前揭註 19,頁 299。
25 許志雄,結社自由與違憲審查─司法院釋字第 644 號解釋評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163 期,2008 年 12 月,
頁 176。
26 參考,Wolfgang Rüfner 著,蔡震榮譯,基本權利的個人關聯性與法人的基本權利保護,收錄於 Peter Bad-
ura、Horst Dreier 主編,蘇永欽等譯注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下冊),聯經,2010 年 10
月,頁 67-69
27 李震山,前揭註 4,頁 174-177。
28 李建良,憲法變遷中的原住民族權利─原住民族自治權的法理基礎,憲政時代,第 31 卷第 1 期,2005 年 7
月,頁 12-13。
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