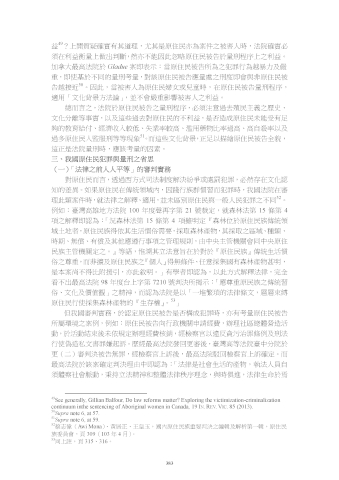Page 389 - 第七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389
49
益 ?上開質疑確實有其道理,尤其是原住民亦為案件之被害人時,法院確實必
須在利益衡量上做出判斷,然亦不能因此忽略原住民被告於量刑程序上之利益。
加拿大最高法院於 Gladue 案即表示:當原住民被告所為之犯罪行為越暴力及嚴
重,即使基於不同的量刑考量,對該原住民被告應量處之刑度即會與非原住民被
50
告越接近 。因此,當被害人為原住民婦女或兒童時,在原住民被告量刑程序,
適用「文化背景方法論」,並不會嚴重影響被害人之利益。
總而言之,法院於原住民被告之量刑程序,必須注意過去殖民主義之歷史、
文化分離等事實,以及這些過去對原住民的不利益,是否造成原住民未能受有足
夠的教育給付、經濟收入較低、失業率較高、濫用藥物比率過高、高自殺率以及
51
過多原住民入監服刑等等現象 。而這些文化背景,正足以描繪原住民被告全貌,
這正是法院量刑時,應該考量的因素。
三、我國原住民犯罪與量刑之省思
(一)「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審判實務
對原住民而言,透過西方式司法制度解決紛爭或處罰犯罪,必然存在文化認
知的差異。如果原住民在傳統領域內,因踐行族群慣習而犯罪時,我國法院在審
52
理此類案件時,就法律之解釋、適用,並未區別原住民與一般人民犯罪之不同 。
例如: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0 年度聲再字第 21 號裁定,就森林法第 15 條第 4
項之解釋即認為:「況森林法第 15 條第 4 項雖明定『森林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
域土地者,原住民族得依其生活慣俗需要,採取森林產物,其採取之區域、種類、
時期、無償、有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
民族主管機關定之。』等語,惟溯其立法意旨在於對於『原住民族』傳統生活慣
俗之尊重,而非擴及原住民族之『個人』得無條件、任意採集國有森林產物甚明,
是本案尚不得比附援引,亦此敘明。」有學者即認為,以此方式解釋法律,完全
看不出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7210 號判決所揭示:「應尊重原民族之傳統習
俗、文化及價值觀」之精神,而認為法院是以「一堆繁瑣的法律條文,層層束縛
53
原住民行使採集森林產物的『生存權』。 」
但我國審判實務,於認定原住民被告是否構成犯罪時,亦有考量原住民被告
所屬環境之案例,例如:原住民被告向行政機關申請經費,辦理社區總體營造活
動,於活動結束後未依規定辦理經費核銷,經檢察官以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及刑法
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起訴。歷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後,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
更(二)審判決被告無罪,經檢察官上訴後,最高法院駁回檢察官上訴確定。而
最高法院於該案確定判決理由中即認為:「法律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執法人員自
須體察社會脈動,秉持立法精神和整體法律秩序理念,與時俱進,法律生命於焉
49
See generally, Gillian Balfour, Do law reforms matter? Exploring the victimization-criminalization
continuum inthe sentencing of Aboriginal women in Canada, 19 IN. REV. VIC. 85 (2013).
50
Supra note 6, at 57.
51 Supra note 6, at 59.
52 蔡志偉(Awi Mona)、黃居正、王皇玉,國內原住民族重要判決之編輯及解析第一輯,原住民
族委員會,頁 309(103 年 4 月)。
53 同上註,頁 315、316。
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