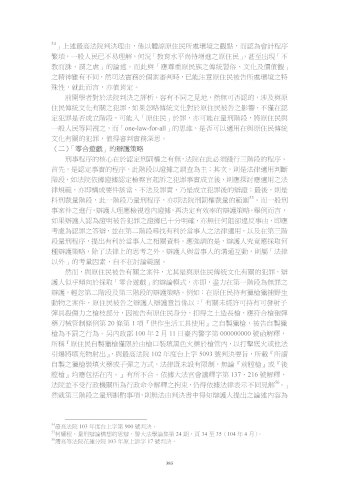Page 391 - 第七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391
54
」上述最高法院判決理由,係以體諒原住民所處環境之觀點,而認為會計程序
繁瑣,一般人民已不易理解,何況「教育水平尚待增進之原住民」,甚至出現「不
教而誅,謂之虐」的論述。而此與「應尊重原民族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
之精神雖有不同,然司法實務於個案審判時,已能注意原住民被告所處環境之特
殊性,就此而言,亦值肯定。
前開學者對於法院判決之評析,容有不同之見地,然無可否認的,涉及與原
住民傳統文化有關之犯罪,如果忽略傳統文化對於原住民被告之影響,不僅在認
定犯罪是否成立階段,可能入「原住民」於罪,亦可能在量刑階段,將原住民與
一般人民等同視之,而「one-law-for-all」的思維,是否可以適用在與原住民傳統
文化有關的犯罪,值得審判實務深思。
(二)「零合遊戲」的辯護策略
刑事程序的核心在於認定刑罰權之有無,法院在此必須踐行三階段的程序。
首先,是認定事實的程序,此階段以證據之調查為主;其次,則是法律適用判斷
階段,如法院依據證據認定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成立後,則應探討應適用之法
律規範,亦即構成要件該當、不法及罪責,乃是成立犯罪後的辯證;最後,則是
55
科刑裁量階段,此一階段乃量刑程序,亦即法院刑罰權裁量的範圍 。而一般刑
事案件之進行,辯護人理應檢視卷內證據,再決定有效率的辯護策略。舉例而言,
如果辯護人認為證明被告犯罪之證據已十分明確,亦無任何阻卻違反事由,即應
考慮為認罪之答辯,並在第二階段尋找有利於當事人之法律適用,以及在第三階
段量刑程序,提出有利於當事人之相關資料。應強調的是,辯護人究竟應採取何
種辯護策略,除了法律上的思考之外,辯護人與當事人的溝通互動,則屬「法律
以外」的考量因素,自不在討論範圍。
然而,與原住民被告有關之案件,尤其是與原住民傳統文化有關的犯罪,辯
護人似乎傾向於採取「零合遊戲」的辯論模式,亦即,盡力在第一階段為無罪之
辯護,輕忽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的辯護策略。例如:在原住民持有獵槍獵捕野生
動物之案件,原住民被告之辯護人辯護意旨係以:「有關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
彈具殺傷力之槍枝部分,因被告有原住民身分,扣得之土造長槍,應符合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供作生活工具使用』之自製獵槍,被告自製獵
槍為不罰之行為。另內政部 100 年 2 月 11 日臺內警字第 000000000 號函解釋,
所稱『原住民自製獵槍僅限於由槍口裝填黑色火藥於槍管內,以打擊底火或他法
引爆將填充物射出』,與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 5093 號判決要旨,所載『所謂
自製之獵槍裝填火藥或子彈之方式,法律既未設有限制,無論『前膛槍』或『後
膛槍』均應包括在內。』有所不合。依據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37、216 號解釋,
56
法院並不受行政機關所為行政命令解釋之拘束,仍得依據法律表示不同見解 。」
然就第三階段之量刑斟酌事項,則無法由判決書中得知辯護人提出之論述內容為
54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900 號判決。
55 柯耀程,量刑辯論構想的思辯,警大法學論集第 24 期,頁 34 至 35(104 年 4 月)。
56 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3 年原上訴字 17 號判決。
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