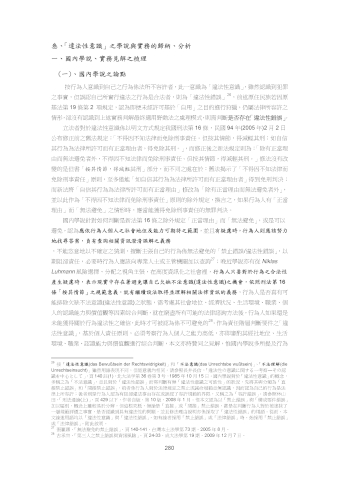Page 284 - 第五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
P. 284
叁、「違法性意識」之學說與實務的歸納、分析
一、國內學說、實務見解之梳理
(一)、國內學說之論點
按行為人意識到自己之行為係法所不容許者,此一意識為「違法性意識」,雖然認識到犯罪
26
之事實,但誤認自己所實行違法之行為是合法者,則為「違法性錯誤」 ,前述原住民族若因原
基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認為即便未經許可基於「自用」之目的進行狩獵,仍屬法律所容許之
情形,卻沒有認識到上述實務判解最終適用野動法之處理模式,則需判斷是否存在「違法性錯誤」。
立法者對於違法性意識係以明文方式規定我國刑法第 16 條,民國 94 年(2005 年)2 月 2 日
公布修正前之舊法規定:「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如自信
其行為為法律所許可而有正當理由者,得免除其刑。」,而修正後之新法規定則為:「除有正當理
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修法沒有改
變的是但書「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部分,而不同之處在於:舊法揭示了「不得因不知法律而
免除刑事責任」原則,至多僅能「如自信其行為為法律所許可而有正當理由者」得到免刑判決;
而新法將「自信其行為為法律所許可而有正當理由」修改為「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
並以此作為「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原則的除外規定,換言之,如果行為人有「正當
理由」而「無法避免」之情形時,應當能獲得免除刑事責任的無罪判決。
國內學說針對如何判斷是新法第 16 條之除外規定「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或是可以
避免,認為應依行為人個人之社會地位及能力可期待之範圍,並且有疑慮時,行為人則應該努力
地找尋答案,負有查詢相關資訊澄清誤解之義務
,不能恣意地以不確定之猜測,擅斷主張自己的行為係無法避免的「禁止錯誤/違法性錯誤」,以
27
期阻卻責任,必要時行為人應該向專業人士或主管機關加以查詢 ;晚近學說亦有從 Niklas
Luhmann 風險選擇、分配之視角主張,在高度資訊化之社會裡,行為人只要對於行為之合法性
產生疑慮時,表示現實中存在著避免讓自己欠缺不法意識(違法性意識)之機會,依照刑法第 16
條「按其情節」之規範意義,就有繼續設法取得並理解相關法律資訊的義務,行為人是否真有可
能排除欠缺不法意識(違法性意識)之狀態,需考慮其社會地位、經濟狀況、生活環境、職業、個
人的認識能力與價值觀等因素綜合判斷,就在窮盡所有可能的法律諮詢方法後,行為人如果還是
28
未能獲得關於行為違法性之確信,此時才可被認為係不可避免的 。作為責任階層判斷要件之「違
法性意識」,基於個人責任原則,必須考察行為人個人之能力高低,亦即審酌其經社地位、生活
環境、職業、認識能力與價值觀進行綜合判斷,本文亦持贊同之見解,惟國內學說多所提及行為
26
按「違法性意識(das Bewußtsein der Rechtswidrigkeit)」和「不法意識(das Unrechtsbe wußtsein)」、「不法理解(die
Unrechtseinsucht)」雖然用語表現不同,但是意義均相同。請參照長井長信,「違法性の意識に関する一考察―その認
識を中心として」,頁 140 註(1),北大法学第 36 卷第 3 号,1985 年 10 月 15 日。國內學說對於「違法性意識」的概念,
多稱之為「不法意識」,並且對於「違法性錯誤」而需判斷有無「違法性意識之可能性」的狀況,先將其與分類為「直
接禁止錯誤」和「間接禁止錯誤」,前者係行為人對於法律規定之禁止或誡命規範並無認識,因而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法
律上所容許;後者則是行為人認為有阻卻違法事由存在或誤認了容許規範的界限,又稱之為「容許錯誤」。請參照林山
田,「刑法通論(上)」,頁 429 以下,作者自版,第 10 版,2008 年 1 月。惟本文認為以「禁止錯誤」與「構成要件錯誤」
加以區別,概念上雖較易於分辨,但追根究柢,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禁止錯誤,都是在判斷行為人對於被塗抹了
一層規範評價之事實,是否認識到具有違法性的問題,並且修法理由說明亦係採取了「違法性錯誤」的用語。從而,本
文論述用語均以「違法性意識」與「違法性錯誤」,如有論者採用「禁止錯誤」或「法律錯誤」時,始採用「禁止錯誤」
或「法律錯誤」,附此敘明。
27
張麗卿,「無法避免的禁止錯誤」,頁 140-141,台灣本土法學第 73 期,2005 年 8 月。
28
古承宗,「第三人之禁止錯誤與資訊風險」,頁 24-33,成大法學第 19 期,2009 年 12 月 7 日。
280